剖心记 吴趼人著 第一回增感触开卷述原因惓孝友立身定基础 近年以来,自从新小说发起之后,一时小说之作,风起云涌,数年之间,翻译的、自撰的,真是汗牛充栋;就是在下瞎胡说诌的,也不下五七种了。其中如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虽是东施效颦,却幸得看官们还不以为丑,所以近日又触动了一件事,要撰这部法律小说了。却是为甚么事触动起来的?看官们且听我道来。 近来朝野上下,不是天天说化除满汉轸域么?也有臣工建言的,也有百姓上书的。在下敢说一句话,是言之非艰,行这维难罢了。大凡一件事情出来,无论大小,总要说得出、办得到才是个道理。我看得化除满汉这件事,不过政府不做罢了。政府既然不做,这些旁边人,凭你建言的建言,上书的上书,有甚么用处!各人所建的言,所上的书,在下也曾从报纸上得看见过来,内中不是陈陈相因的腐谈,便是不能实行的办法。我最佩服的是皖抚冯梦华中丞所上的折子,有两句说:“伏乞皇太后、皇上以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为心,不独无歧视满汉之见,亦并无化除满汉之见。”又有两句说是“臣尤愿我皇太后、皇上立贤无方,实事求是,但论贤否,不论亲疏”。这几句说话,真是化除满汉的妙药,整顿内政的金针,看了真是令人五体投地!我因为看了这几句话,就触动了心事,要撰这部法律小说。 因为皖抚冯中丞,我却又想起前任皖抚恩中丞来。这位恩中丞被徐锡麟刺死了,恩中丞手下的人,拿了已经抵罪的徐锡麟来剖心致祭。但是社会上的人,都说是“野蛮,野蛮”。依在下说起来,野蛮不野蛮,我是分辨他不出来。剖心致祭,虽然没有这条法律,然而返躬自问,譬如此刻出了一个大有造于中国的英雄,眼看着强国强种,文明进化,一切种种都是他提倡的,他又能设法实行,一旦无端被刺客杀了,只怕社会诸公,也未尝不想拿这刺客剖心致祭呢!若是权力办得到,也未尝不想实行剖心致祭呢。再说得近一层,譬如我的父,无端被人刺杀了,为人子者拿住了这个仇人,岂有不想生啖其肉之理!只怕剖心致祭,还安放在第二着呢。恩中丞虽然不能比得大英雄,更比不得我父,然而人物虽然不同,其所亲之感情,是无有不同的。我因为这件事,又加上一层感触,要撰这部法律小说《剖心记》。做书的缘由表明,且看我叙这卷信而有征、毫不捏造的法律小说正传。 却说乾隆五十年乙巳,这一年山东莱州府府考。这位郡侯甘太尊,是一位爱材若渴的贤太守,在各考童卷中,看见一卷文字清真、书法严整,翻转看看卷面,心中甚是欢喜,便取在前列招复。到了堂复那天,这位甘太守高坐堂皇,细细留心察看,看见一个考童,年在十四五上下,两眸炯炯,举止庄重,便留心看着。只见他笔不停挥,不多一会儿,便誊正交卷。甘太守一面要他的卷,看了一看,一面招呼来至案下,问道:“你便是即墨李毓昌么?”应道:“是。”甘太守道:“十四岁的年纪是真的么?”应道:“是。童生十四岁,不敢虚报。”甘太守道:“你考过了试,还回即墨么?”应道:“是。”甘太守道:“我看你文字很好,举动也端凝。这府城里海山书院的山长张太史品学兼优,我看你与其回即墨,不如就在海山书院读书,专等宗师按临,岂不省了往来跋涉。”李毓昌想了一想,未及回言。甘太守道:“你若肯往那里读书,我这里拿片子送你进去。”李毓昌只得拜谢了。甘太守大喜,即给了一张名片,道:“你回到下处,就连行李搬到书院里去。我这里即刻叫人到张先生那里去知照。” 李毓昌领了名片,谢了出来,心中一路踌躇不定,怏怏回到寓所,出了一回神。只见同寓的一个考童也回来了,问道:“荣轩,你笔下怎么这等快?场场都是你先交卷。甘太尊和你说话,可是叫你到海山书院读书?”李毓昌讶道:“莲峰兄,你怎么便知道了?”莲峰道:“我如何得知!是我交卷时,太尊叫住问我:‘既是李毓昌同县,可曾相识?’我回说:‘一向相识,这回还是同寓。’太尊便叫我和你同去海山书院读书,所以我才知道了。”李毓昌道:“你去不去?”莲峰道:“这是太尊的另眼,如何不去!”李毓昌道:“我本自打算不去了,也是为着太尊好意,不便过却。”莲峰道:“这有甚不去!难得遇了太尊青眼,我们依着他,在这里用功,将来宗师按临,得他吹嘘吹嘘,好歹与我们前程方便。”李毓昌正色道:“莲峰兄,那里话来,我辈读书,科名自有定分,若当此进身之始,便想仗着他人吹嘘,便先成了个患得患失的鄙夫了。”莲峰听说,满面羞惭,连忙谢过道:“荣轩兄,这是我得意之后偶尔失言,望勿见罪。你若是肯留在这里,我也情愿在这里相随,早晚请教。若是你不愿留,我们且等发了案,一同回即墨也罢。”李毓昌道:“太守既有此好意,我们也不便过于矫情,只得暂留在这里,将来见机而行罢了。”莲峰听说,也就无言。当下在寓过了一夜。次日清晨,二人起来,带了帖子,走到海山书院,拜见山长张太史。 张太史接着两张贴子,一张是李毓昌,一张是林挺岳,连忙接见。行礼已毕,张太史先说道:“昨日太尊来知照过,说二位英年馆学,不胜钦仰,此后彼此同研,正好借重切磋。还未请教二位台甫。”李毓昌便道:“学生贱字荣轩。”林挺岳道:“小字莲峰。”荣轩又道:“承太尊推荐,得先生收在门下,朝夕得侍绛帐,尚乞不吝教诲。”张太史谦逊了几句,便叫搬到书院里来住。李、林二人即便回寓,取了行李,搬到书院,重新请了张太史出来,行了师生大礼,从此就在书院用功。 过了几时,府案发了出来,李毓昌取了案首,林挺岳也在前列。林挺岳不胜欢喜,便是张太史也觉着高兴。只有李毓昌行所无事。张太史见了他这等凝重,不禁暗服甘太守拔识得人。 光阴荏苒,早已过了两个月。一日,李毓昌走到张太史房里,禀告道:“门生到此两月有余,多承先生耳提面命,本应常侍函丈,自求进益。争奈门生家里有事,意欲请假回去一次。望乞先生鉴谅。”张太史道:“正是。我一向不曾问得,你家中还有何人?你才得十四岁,除了用功读书之外,还有甚事?”李毓昌见问,眼圈儿一红道:“门生幼失怙恃,只有祖父在侍,年已八十余岁,老人多病,常须伏侍。幼弟今年七岁,家贫不能从师,早晚皆由门生指授认字。只此便是门生的事。”张太史道:“如此不敢强留,但是你也当到甘太尊处告辞一声。”李毓昌道:“读书人不便无事入公门,甘太尊处求先生便中代禀一声也罢。”张太史道:“那么你几时动身?”李毓昌道:“只求先生准了假,明后天都可以动身。”张太史道:“既如此,我不便阻你,你索性后天走罢。等我明天去见太尊,先代你告辞,也是个礼节。”李毓昌听说,连忙拜谢。未知李毓昌回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掇芹香知己遇恩师折荆枝孔怀伤幼弟 且说李毓昌当下辞了张太史,自加斋舍,便告知林挺岳请假回去的话。林挺岳惊道:“你既然请假回去,为甚不告诉我?”李毓昌道:“我自要回去,你不见得也要回去,何必告诉你呢?”林挺岳呆了一呆,也不言语,起身去见张太史,也要请假回籍。张太史讶道:“荣轩要请假,说是因为祖父年高,幼弟待教,你却又有何事?”林挺岳道:“不瞒先生说,门生和荣轩,起初是文字之交,近来同研两月,朝夕亲炙,方知道荣轩是一个方正君子,门生心中已认定他是一个益友。因听说他要请假回籍,所以门生也要跟着回去,打算同在乡里,可以时常亲近的意思。”张太史道:“荣轩不但举止端重,并且天性过人,你愿与他为友,也是你的长处。那么你们一起走罢。”挺岳拜谢了,回到斋舍,告知毓昌。毓昌道:“你在这里用功很好,如何也要回去?”挺岳道:“我也思家念切,所以趁此搭伴同行,在路上彼此也不寂寞。”毓昌听说,也就不再多言。 到了次日,张太史到府里去了回来,便请李、林两个到自己斋内,告诉说,已代回过府尊,府尊切嘱转致荣轩,回去上紧用功,不可荒废;又每人送与程仪京钱十千,聊作膏伙之助。说罢捡出钱贴,交与二人。二人拜谢了,便各自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当夜毓昌与挺岳商议道:“承莲峰兄雅意,与我结伴同行,但是也有不方便的去处:我是寒素人家,不能不事事撙节,不能比你。我明日打算自己背了行李,步行回去,你只怕还不能与我同行呢。”挺岳道:“岂有此事,难道你走得,我便走不得么?我便陪着你走便是。”毓昌道:“这个不行,你是走不惯的,恐怕走伤了,岂不是我害你的么?”挺岳沉吟道:“你既然念着祖老大人,急于回去,步行未免耽搁了。我们不如同雇一辆车子,赶路又快,在车上又可以谈天,岂不是好?你如果嫌费,这车价都归了我出如何?”毓昌道:“这个断无此理。”说罢,又沉吟了一会道:“其实我近来心惊肉跳,这些虽然是思家所致,然而归心似箭,总想早点见了祖父,方才安心。同雇一辆车子也好,不过车价断没有归你一个人出之理,总要合出才是。”挺岳也含糊答应了,一宿无话。次日二人起来,雇定了车,拜辞了张太史,并求代为向甘太尊道谢,话别一番,登车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到了即墨。毓昌回到家中,见了祖父,问知向日安健,自是欢喜。又见过庶母韩氏。韩氏便叫幼子毓材过来拜见哥哥。自此一家团叙。毓昌因为课弟之便,就在家中设个蒙塾,招几个学生,坐起馆来。这回他府考取了案首,又蒙本府另眼相待,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有学问的,所以年纪虽轻,来从学的人却也不少。毓昌收了几处贽见束修,又考了两课书院,取在前列,得了奖赏,凑起来,拿到挺岳家中,还他前次由府里回来的车费。挺岳道:“这些微小费,何必介怀,我决不收受。”毓昌道:“本来到了家时,就当奉缴,因为前回府尊送的十吊京钱,与及自己身边带的一吊多钱,在路上失去了,所以耽搁到今日,方能奉还。”挺岳讶道:“是在那里失去的?何以在路上并未听见说起?”毓昌道:“是在宿站上失去的,已经失了,说他做甚么。”挺岳顿足道:“你也过于迂腐了,失了之后,便当说出来,叫地保去查,倘使查不出来,好歹要客店里赔我。怎么一言不发,就这么过去了?”毓昌道:“莲峰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偷我几吊钱的人,自然比我还穷,方才出这个下策。倘使一经张扬起来,查明白了,岂不是令其无地自容。所以我索性不去声张,正是留他一点地步。君子与人为善,何处不可行我的恕道。至于要客店赔偿,那更是非理的举动了。”挺岳肃然起敬道:“荣轩兄真是现在的古人,我深愧不如。至于这点点车,譬如我自己一个回来,也要用的,决不敢受,请拿回去,聊佐膏伙之费。”毓昌道:“这个断无此理。岂不闻廉洁之士,一介不取,莲峰难道不准我行其素志么?”挺岳沉吟半晌道:“荣轩兄,你是个廉洁之士,我不敢相强。但是古人朋友相处,也有分金之义,这个钱,你只算我已经受了,转送与祖老大人,作为助你的甘旨之奉如何?”毓昌听说,便道:“承莲峰兄如此见爱,我虽不敢过却,尚待回去禀过家祖,方才敢受。”说罢辞了回家,见过祖父,禀知上项事情。祖父道:“你自不小心,把钱失去,既负了太尊盛情,又耽搁了莲峰许久,既然凑了出来,自然还了他为是。但是他既如此相谅,知你一定不肯收还,却说送与我的,你若再推辞,又似过于矫情了,只得受了他。不过受人之惠,不可忘报罢了。”毓昌唯唯听命,又再到莲峰处拜谢了。 光阴荏苒,不到几时,县中接了公事,知道宗师将近按临莱州了。一从考童听了这个消息,莫不磨砺以须。毓昌也辞了祖父,约了莲峰,同伴取道到郡城来,仍旧到海山书院住下,拜见了张太史,专等入场考试。 话休烦絮,专场已过,发出案来,挺岳进了邑庠,毓昌却进了郡庠案首。簪花谒圣之后,甘太守专请了毓昌去衙门里,勉励一番道:“这回是兄弟在宗师面前竭力保你,又求他拔了你入郡庠。我看你言动举止十分端重,在海山书院两个月,张太史也极赞你的人品好,此刻的时世,文章易得,品行难求,所以我也乐得收一个优行门生。望你从此益加勉励,做一个完人。”毓昌感恩知己,拜谢不已。辞了出来,仍旧和挺岳结伴,回到即墨,见过祖父。亲友都来贺喜,自不必言。 大凡人事,总不能十分圆满。当着那科举时代,李毓昌不过一个十四岁孩子,被本府另眼相待,进了郡庠案首,这是何等荣幸,何等快活的事!当时一众乡邻亲友,那个不说他前程远大,后福难量;便是他那八十多岁的祖父,看见了自然也是欢喜无穷。那蒙塾之中,因为他进了学,凭空也多添了十多个学生。那些有女儿的人家,也都托了媒人来说亲。你说热闹不热闹! 谁知他进学回来不多几日,他的幼弟毓材,便得了个外感的病。即墨地方本来没甚名医,因为毓昌进学回来,众亲友都送了贺礼,不免置酒请了一天客,那医生拿了这个用神,以为小孩子多吃了肥腻之品,停食在内,开出方子来,药不对症,那外感便传了入里,一天重似一天,任从毓昌十分用心调护,韩氏尽力提携,只因自己不曾懂得医理,便误了事,到了十多天,再也捱不过去,便自死了。韩氏未免儿天儿地的大哭起来,毓昌也不免号啕大哭。毓昌的祖父是年老的人,一听见小孙子不好了,吃了一惊,扶了拐杖,颤巍巍的忙着来看,不期心忙意乱,立脚本不甚稳,又且急步匆匆,被门阆绊了一交。毓昌正在哭叫小兄弟,听说祖父跌了,吓得魂不附体,忙忙跑来看视。不知有无性命之虞,且听下回分解。 全书完
 下旋
下旋 左旋
左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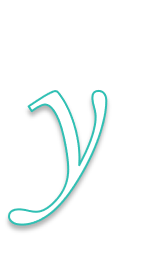 上旋
上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