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言 王国维 (一)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古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以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污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餔錣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二)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放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錣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放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玄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錣的文学之记号也。 (四)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遂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六)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眼睍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九) “驾波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 (十一)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十二)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 (十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僕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 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錣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錣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国学丛刊序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幾《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如各史文苑传。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且于一学之中,又择其一部而从事焉。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学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学、真为学者,可信其无是也。 夫然,故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可得而详焉。何以言学无新旧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弃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无用之论,则比前二说为有力。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偏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尠。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王国维<<元曲之文章>>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龠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词,固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节选自《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安《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寻往迹,诚难诚难。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使臧晋叔未尝刻此,则今人竟不能知元剧为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籀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今撮录如次——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 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 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 “臧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 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 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 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 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 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 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 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 《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 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 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 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 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 剧中,亦无媿色也。(按,即此而论可见中国戏剧历 代退化。)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 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 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 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 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 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 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至于今日,中国声乐之学,衰息极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则此书而外,更应撰论述明南曲之书词之来源与变化,汉魏以来,至于明清声乐之迁嬗,亦应有专书论次。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Loczy教授,曾随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访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严之上,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叹洛氏之言不诬。窟穴大小殆以百数,高下成列颇不整齐,石色纯黑,上施雕凿,洞之大半,皆有画壁,美丽殊伦,完缺不一;绘画之法源自身毒。余于和田沙漠所掘废寺佛画,规摹气韵,大略相同,造像之多,与画壁等,可证古代支那印度美术交通;惜多为后人补葺,失其真矣! 严洞之傍,颇多碑碣,证此古寺建于唐代,当时佛教盛于支那。又二百年间,西陲无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讫于蒙古之兴,则外常为蛮族之所蹂躏。寺宇之丽,僧尼之数,为之大减矣!顾情势虽变,而宗教未革。余周览各洞,多见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种制作,稍属后代。读《马哥波罗旅行记》中《沙州》一篇,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二) 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见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元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耳!虽荒唐之西游记,视元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元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元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三)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伺,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见印度婆罗谜草书Indian Brahmi So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像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见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馀晷,以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损。后见道士观此唐代遗物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见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叶,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Pothis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开突厥文Kok-turki及叙利亚文Syriac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斥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始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五) 余以多日之劳,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而选写本图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虽道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又清理全室之事,虽胆壮者犹为寒心,况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未果,于室下得画绢若干束,又于汉文卷中得中亚细亚婆罗谜文,及他文写本等。此处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为彼有。而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人知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兹不暇述。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暂至敦煌,验其名望,不减于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购此,将以佛教之文学美术播于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后此灭亡之厄,甚盛业也。余四月以后,复至兹寺,道士对余无异词,余心尤慰。迄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 余于六月中旬,始毕千佛洞画壁造像之摄影。古物之研究告终,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检。此次事业自南山始,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脉。此脉实苏勒河与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于乔梓村畔两小山脉之间,发见大废址,昔有运河导川至此,遗迹犹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见。天时人力,全由乾燥而变,其初盖可想矣! 是处暴风间作,沙山颇峻,故掘地之事,苦于难施。然由古物上之证据,知此废城在耶稣纪元后十二三世纪,尚有居人,其残垣之存者,尤足证数百年来之风力,面东之坦为飞沙冲击,残毁无余;而南北二垣与东风平行者,尚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即大西河横绝外山脉之处,又有洞宇无数,谓之万佛峡,今日犹为瞻礼之所。庙貌之古,仿佛千佛洞,画壁极大,亦甚完全,作于第八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更足印证当时之佛教画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六) 自是以往,高峰相衔,巅戴冰雪,俯视疏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测量既竟,下至昌马。旋渡昌马河,经未探险之山地。虽在夏季,犹以乏水为苦,遂由嘉峪关入长城。余于此又得决古长城之疑问焉。夫今日中西图籍,均以肃州西南边墙,讫于南山之足者,为古长城尾。又数世纪以来,西域人之访嘉峪关者,无不以是处为中国本部门户。然据中国古书,则关城当远在其西。余于敦煌沙迹中,所发见之古长城遗筑,更足征实此说也。苟一细思,其疑立释。盖嘉峪关附近,实二种防御线之交点;此二线之建筑年代不同,宗旨亦异。一线来自甘州肃州之北,本与安西之长城相接,乃纪元前二世纪所筑也;筑城之旨,在保障南山阴之狭地,及前汉以后,国力更张,此地遂为自中国入西域之孔道。第二线则与第一线互为直角,即嘉峪关城,此后世所筑;其旨在塞西域通路,盖中国守闭关主义以后矣! 余久往肃州,至七月杪始启行,探中部南山。盖地方官吏于余虽甚亲厚,然惧南山寇盗,不任余行,坚请而后可,而转运之事尤多阻碍。甘肃人民以山外之地为人迹所不至,颇惮于行。后虽以官力雇得夫役骡马,皆以早归为约,故唯于利区托芬Richthofen Range 及托雷Tolai Range 两山脉间地,得有向导。此距海面一万三千尺之处,见有金穴,西宁之民在此淘洗云。 余离金矿,正值雪融之际,自是以往,不见人迹。是月之杪,始见蒙古人牧地数处,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堀起,而南走哈喇淖尔及青海间也。其地有四山脉,界画分明,中间山谷亦颇开广,故虽无向导,而不至迷失,测量之事亦颇便利。所过牧地,在距海面万一千尺至万三千尺之间,人畜饥疲,为之苏息。惟大谷之中,空气蒸湿,与南山西部绝异。霰雪日降,道路泥泞,行路之难盖可知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七) 天然之阨既如是矣!重以中国圉人,畏惧艰险,出于天性,视此山中危险,充塞闻见之外,加以想像,群思遁逃,不止一次,余与蒋君且抚且励,始得无事。彼等如年老之人,历险既多,畏事愈甚,及偶值危地,则又如群孩在林,不知所措,故蒋君与余恒谓之曰年老之孩。肃州官吏所派护兵亦然。又赢粮不多,中途自困。适余携有大麦,本用饲马,遂以给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口,蒋君取而食之,然后敢食;后猎得野骡,遂以获济。 自肃州启行后,已行四百余英里,至八月后,乃测量中部南山迤北之三山脉。此三山脉之经度,在甘州肃州之间,高峰戴雪,距海面万八千尺至万九千尺,凡疏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于冰岭之中,余所取之道,务与俄国探险家奥伯拉启甫 M . Obruheff 及哥兹老夫Dozloff异路。三脉中偏南一脉,冠以冰雪,此疏勒河与哈喇淖尔青海水源分界之处,余辈测量,循其北面秀峰连岭,皆高于其北二山脉,其间山谷亦高至万三千英尺,疏勒河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发源之高地,此河乃黄河最北之大源。故余于此处实触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得区托芬之连岭,谷中水势泛滥,行李颇艰。然弥望茂林,大半枞树蔽亏坡麓间,与西部南山之荒凉寒互迥殊。伙伴印人兰沁Ram Singh专司测绘之事,其图中所测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万四千英方里云。 余于九月初,自甘州长行,拟至塔里木河域,以从事第二次冬期探险。此行为调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鲁番之骆驼大道,往来西域者不由罗布淖尔,而由此道,盖已千三四百作年矣!余于甘州至安西途中,时折而北,以探长城遗址,知古之长城,实极于安西。是春夏间之所想像者,遂实证之矣!及抵安西间,沁体弱不堪冬行,乃令其由和阗归印度,便道测敦煌至若羌Charklik(在罗布淖尔之南)之连山,而以拉尔沁Rai Lai Singh从余行,拉氏曾从事异门Yemen至中东部之测量,甚以劳动及精细著者也。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 安阳所出龟甲兽骨,皆刻商代卜辞,文字奇古,比彝器古文尤为难读。光绪季年,丹徒刘氏拓印所藏甲骨为《铁云藏龟》,于是世始知有此物,瑞安孙仲容徵君诒让为之《札记》。宣统元年,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卜辞文字始有条理可寻。参事东渡后,复拓印所藏甲骨为《 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殷墟书契精华录》一卷。去年岁杪,其《殷墟书契考释》 始成,于是卜辞文字可读者,十得五六。盖 近 世 之 言 古 文 者,以 此 书 为 最 善 矣。参事《自序》 曰:宣统壬子冬,余既编印《 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 六万余言。既竟,爰书其端曰:予读《诗》《书》 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 孔子学二代之礼,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献之无徵,二千余年前,则已然矣。吾侪生三千年后,乃欲根据遗文,补苴往籍,譬若观海,茫无津涯。从事稍久,乃知此事实有三难:史公最录商事,本诸《诗》《 书》,旁览《 系本》。顾考父所校,仅存五篇,书序所录,亡者逾半。《系本》一书,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难一也。卜辞文至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谊益难知。其难二也。古文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或数语之中,倒写者一二,两字之名,合书者七八。体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难三也。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小篆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局鐍为开,稽其所得,则有六端: 一曰帝系。商自武汤,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大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较以前史,并与此异。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所未知。此足资考订者一也。 二曰京邑。商之迁都,前八后五。盘庚以前,具见《书序》。而小辛以降,众说多违。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徙于武乙,去于帝乙。又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国尚号商。书曰戎殷,乃称邑而非称国。此可资考订者二也。 三曰祀典。商之祀礼,迥异周京,名称实繁,义多难晓。人鬼之祭,亦用柴2 。牢鬯之数,亦依卜定。王宾之语,为《 洛诰》 所基。3 刚之荐,非镐京所创。此可资考订者三也。 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4 者,则依4 名。又大事贞龟,小事骨卜。凡斯异例,先儒未闻。此可资考订者四也。 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具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资考订者五也。 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4 非睪。鸟鸣之字,从鸡非鸟。佳鸟不分,子5 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二篆,多同古文。古文之真,间存今隶。此可资考证者六也。 予爰始操翰,讫于观成,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以兹下学之资,勉几上达之业。而既竭吾才,时亦弋获,意或天启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赜索隐,疑蕴尚多。覆篑为山,前修莫竟,继是有作,不敢告劳,有生之年,期毕此志。订讹补阙,俟诸后 贤。他山攻错,1予望之。 (某些打不出的字以阿拉伯数字代替) 罗振玉流沙坠简序 予与罗叔言参事,考证流沙坠简,近始成书,罗君作序,其文乃类孔仲远《 诸经正义序》 及颜师古《汉书注序》,兹并录之。曰: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人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板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顾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作而叹曰:千余年来,古简策见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石。顾厘冢遗编,亡于今文之写定;楚邱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檄,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渐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先,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或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 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代迁,证许祭酒之说。是亦名物艺事,考镜所资, 如斯之类,偻指难罄。惟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艺术,僧雯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于编摩,蠡测管窥,裨益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京博士及王君先后述作之初心也。 人间才子——王国维网站 收录 尚未校对 殷墟书契考释序 上虞罗叔言参事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海宁王静安为之后序,惟其初稿乃用骈体,笔意渊雅,有北朝初唐人遗意,近时作者,不能及也。其词曰:商遗先生《 殷墟书契》 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炎汉以来,古文简出,孔壁汲冢,与今之殷墟而三。壁中所得,简策殊多,尚书礼经,颇增篇数。然淹中五十六卷,不同于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见于今文者廿九。因所己知,通彼未见,事有可藉,切非至难。而太常所肄,不曲台之书;临淮所传,亦同济南之数。虽师说之重,在汉殊然,抑通读之方,自古不易。至于误厨序,以B为均,文人之作宁人,大邑之书天邑,今古异文而同谬,伏孔殊师而沿讹。言乎释文,盖未尽善。晋世中经,定于荀东。今世所存,穆传而已。读其写定之书,间存隶古之字,偏旁缔构,殊异古文。随疑分释,徒成虚语,校之汉人,又其次矣。其余郡国山川,多出彝器,始自天水,讫于本朝。吕薛编集于前,阮吴考释于后。恒轩晚出,尤称绝伦。愿于创通条理,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也。夫以壁经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汉晋,非绝远之世;彝器多出两周,考释已更数代,而校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乎宣圣之所无徵,史籀之所未见,去古滋远,为助滋寡,欲稽而明之,岂易易哉。 殷墟书契者,殷商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勒于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章畋渔,至于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爰自光绪之季,出于洹水之墟。先生既网罗以入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日,撰为斯编。余受而读之,见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晰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悟一形繁简之殊,起两字并书之例。上池既饮,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陈,斯举隅而三反。颜黄门所谓癒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 由是大乙卜丙,正传写之伪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诹日卜牲之典,王宾有睪之名,賧燎薶沈之用,牛羊太豕之数。损益之事,羌难问夫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徵于商邑。凡诸放佚,尽在敷陈,驭烛龙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扫荒翳,以视安国所隶定,广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难易,功之多寡,区以别矣。是知效灵者地,复开宛委之藏;宏道惟人,终伫台陵之说。后有作者,俟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海宁王国维。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走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宁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放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界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放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放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放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现,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于然哉!
 下旋
下旋 左旋
左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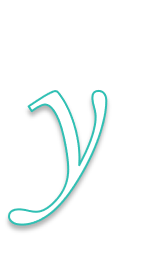 上旋
上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