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濯缨亭笔记》[明]戴冠 《濯缨亭笔记 序》 故绍兴郡学训导戴先生著书一编,曰《濯缨亭笔记》。余为绪正伪阙,除其复重,离为十卷。华学士子潜取而刻之。 戴先生名冠,字章甫,吴之长洲人也。少颖敏笃学。始游乡校,已刻意为古诗文。博览,无所不通。而伉爽负气,高自许与,不能诎折徇物。八举不中,以贡上札部,人试内廷,奏名第一,然例只得学官。 王三原自巡抚江南时,则爱重先生。及是方掌铨,先生贻之书,条刺十事,皆经国大务,语不及私。三原为敛容降叹。李长沙为学士,亦奇其文,皆不及荐也。 在绍兴久之,与贵人语不相下,弃官归。年七十一终于家。濒终犹歌吟不辍。既而叹曰:“天梦梦乎,世掝掝乎,仳倠拥楹娵奢斥乎,矫虔驷驾随夷路乎,已乎,已乎,豪杰者废死乎!”闻者悲之。 先生早有志用世,自兵、农、水利之说,靡不论究,既连蹇弗试,益泄其感愤于文。词廉峭精确,多所风切。平生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得奇文奥义,为抵掌自喜,辄命笔识之。是编所存,仅十二三,盖非其至者。然其扶树教道,绳枉黜邪之指,亦略可睹矣。君子曰:“夫士苟有以信于千载,虽长陨沟壑,不为辱也。”太史迁有言:“俶傥非常之人,意有所郁结,则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若戴先生几是耶! 余少则知慕先生,感风流之日遐,惧遗文之泯坠,爰叙列大校,今后来者得考览焉。 先生尝作《礼记集说辨疑》,未竟,今掇其存者若干章,附之编末。他所纂述,若诗文集尚数十卷,藏其家。 嘉靖丁未(二十六年,公元年)秋七月望前进士邑人陆粲序 《濯缨亭笔记》卷一 太祖高皇帝于中都皇陵四门悬金字牌各一,其文曰:“民间先世尝有坟墓在此地者,许令以时祭扫。守门官军阻挡者,以违制论。”呜呼,此圣人一视同仁,以四海为家之心也。今世少有富贵权力者,每得墓地,有旧冢在,必恩去之,以为福荫子孙之计。至有发掘尸枢而焚毁之者。其视圣祖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元主忽必烈用西僧嗣古妙高及杨琏真加之言,尽发宋诸陵之在绍兴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窃其宝玉无算,截理宗顶骨为饮器。胡主吞灭中国之初,即行此盗贼不仁之事。 我太祖即位之元年戊申正月戊午,即御札丞相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汝纳监藏深惠,诏付应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瘗诸南门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览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图,遂命藏诸旧穴。 时开国之初,庶务方殷,而首求先代帝王之遗骸,若救焚拯溺之不暇,往返数千里,首尾不逾三月,即得旧物归瘗中土;又仅逾年,而即返诸故穴,其敏于举义如此。英明刚果之志,慈祥恻隐之心,虽尧舜汤武,不是过矣。于乎休哉! 诚意伯刘基初见太祖,太祖曰:“能诗乎?”基曰:“诗,儒者末事,何谓不能?”时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筷使赋之。基应曰:“一对湘江玉并看,湘妃曾洒泪痕斑。”帝颦蹙曰:“秀才气味。”基曰:“未也。”复云:“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帝大悦,以为相见晚。 洪武中,绍兴日铸岭有宋侍郎者,尝恃上燕语。上曰:“汝有子读书乎?谁为之师者?”宋曰:“臣妻弟某来谒,臣留于家以教臣子。”上曰:“可令见朕。” 明日,宋与其人俱入见。上谓曰:“汝作字师谁?”对曰:“学智永。”上曰:“何故学和尚字。汝能诗乎?宜为朕赋一诗。”某请题。上曰:“任汝意为之。”某应声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亲旧住京畿。丹心冉冉如云气,常绕黄金阙下飞。”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日拜刑部主事。国初用人如此。 刘政,字仲理,吴县人。洪武己卯南畿乡试,方孝孺为考官,以“论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为题策问,文武并用。孝孺得政卷,赏许甚至,遂为解首。 政为人慷慨,尚气节,尝以豪杰自许。忽得隐疾。值太宗渡江,愤愤不食,力疾起行,以足顿地,意呕血死。可谓不负方公之知矣。 王景,字景章,处州松阳人,草太宗即位诏。或云无锡王达善所草,未知孰是。 宋末沈敬之逃占城乞兵兴复,占城以国小辞。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归。占城宾之而不臣,敬之竟忧愤发病卒。其王作诗挽之,曰:“恸哭江南老矩卿,春风揾泪为伤情。无端天下编年月,致使人间有死生。万叠白云遮故国,一抔黄土盖香名。英魂好逐东流去,莫向边隅怨不平。” 我太宗初承大统,诏谕海外诸国,朝鲜王芳运作诗以献,曰:“紫凤衔书下九霄,遐陬喜气动民谣。久潜龙虎声相应,未戮鲸鲵气尚骄,万里江山归正统,百年人物见清朝。天教老眼观新化,白发那堪不肯饶。” 夫占城以岛夷知重节义如此,朝鲜乃箕子之国,然世远教衰,三仁之风泯矣,悲夫! 永乐间,苏人有沈景旸者,精于卜,用钱三枚,掷以成卦,言无不验。 太宗闻其名,遣内侍乘传来召之。景旸就道,豫卜一卦,语使者曰:“若上得此卦,则无不利矣。” 既至,入见趋急,俯伏喘不能言。上令少休,乃引问曰:“汝术何所本?”对曰:“《周易》。”上曰:“亦不过《周易》。”乃取钱向天默祝,今年竖授景旸。卜之,正得向卦,因具述前语以对,曰:“此卦最利行师,战无不克。”上大悦,令出就舍,需其验而官之。已而师果克捷。 他日,又召景旸卜,卦成,景旸俯首不语。良久,上曰:“何如?”景旸对曰:“不可用。”上不悦,趣令引出,诏有司具驿舟送归,只给楮币、衣帽而已。景旸语人云,“上初筮者,殆匈奴之大部落,后筮者,其小种耳。上意大者既克,于小者何有。然卦实有凶咎,不敢言。”上竟亲征出塞,至榆木川而宫车晏驾矣。 余友华思淳者,无锡人,弘治戊午岁卒,时年九十。自言少时尝从景旸卜,戒思淳诘旦早来。思淳如期往,道逢故人,同于针肆少憩。既至其家,景旸掷钱成卦,问曰:“汝晨餐未?”思淳诡对曰:“已饭。”曰:“若此则卦不灵,须明早更卜。”思淳谢曰:“实未食。”又曰:“汝安得入铁肆中坐?”曰:“无之。”曰:“若此则卦不灵,须明早更卜。”思淳乃复以实告。景旸曰:“若然,则汝还家三日,汝室必生一男子。汝仆怀钱三百,将以遗吾,吾不受。俟生子后来谢未晚也。”越三日,果得男。他奇验多类此。景旸死,无子,其术不传。 己已之变,英庙北狩,郕王居摄,寻即真。先是京师旱,童谣曰:“雨弟雨弟,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谢了土地。”明年,北虏奉还上皇。后七年而复辟。人谓:“雨弟者,与弟也。城隍土地者,言郕王者有土也。雨若再来,谢了土地者,上皇还,而土地复归也。” 景泰间,欲易太子,不爱官爵以悦臣下,一时名器太滥。时人为之语曰:“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似境山猪。” 前史所记:更始时,“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唐武后时,“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谣,与此相类。 天顺八年宪宗初即位时,南京刑科给事中王渊等上言五事,其疏传布四方,冠得而录之,谨识其略如左: 一曰览史书。 史书之有益于天下国家尚矣,求其明白切妥,可为万世之法者,莫如《通鉴纲目》一书。近年以来,经筵唯以五经四书进讲,而不及此,盖恐其间有所触犯故尔。 昔唐仇士良尝语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读书。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今日之事,殆亦类此?乞命讲官兼讲《通鉴纲目》其中所载治乱兴亡,不得避讳。仍取一部置于便殿,万几之暇,朝夕观览。或时召儒臣与之从容讲解,必欲见古之君德何为而明,何为而暗。政治何为而得,何为而失。群臣何者为贤良,何者为邪佞。然后以其善者为法,恶者为戒。仍观左右大臣孰可比古之贤良而当亲,孰可比古之邪佞而当黜。如此则德无不修,政无不善,臣无不良,而天下治矣。 二曰开言路。 皇上嗣登大宝之初,屡下求言之诏矣,然给事中、御史所陈之言,事体不一。其有当行者,大臣以不便己,私托以它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不过苟应故事,致使言为虚文,事无实效。言者见其然,皆曰:言既不行,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能常开者,一也。 至有权奸在位,于进言之人多方箝制,或指为轻薄,或目为狂妄,或索其瑕疵。凡有更张,则曰变乱成法;凡有荐举,则曰专擅选官;凡有弹劾,则曰排陷大臣。或明加谴罚,或阴为中伤。言者见其然,皆曰:非徒无益于国,适足自祸其身。此言路所以不能常开者,二也。 乞敕所司,凡言有当行者,即为之施行,务臻实效,不为虚文。有言不当理者,尤望宏天地之量,宽斧钺之诛,置之不问。如此则言路常开,事无壅蔽,大平可计日而待矣。 三曰重大臣。 所谓大臣者,非才德纯全,心术正大,宽平而识大体,廉洁而不顾己私者,不足以当之。是故未用之先,当重其选。既用之后,当重其人。乞敕吏、兵二部,自今如尚书、侍郎、都御史、大理寺卿、五府都督及在外布政使、按察使、镇守、总兵等官有缺,宜会同内阁大臣、六部、都察院等诸司正官,以公推举,各荐所知,较其优劣,不限资格。公举即定,然后本部具奏定夺。其有荐举不公,许科道纠劾,治以欺妄不忠之罪。盖选用文武官员,固吏、兵二部之事,但大臣非群臣可比,一非其人,则为害不浅。是故一人所知,不若众知者广;一人所举,不若众学者公。 然选文既重,待之尤不可不重。近年以来,大臣有犯公罪者,辄系累下狱,褫衣受刑。不数日,寻复其任。彼方为群僚之表率,使之何施面目以处人上乎!要当视为一体,加以礼貌,其有小过,置之不问;若有大罪,则或黜之为民,或赐以自尽,不可辱于市朝。必元恶大奸然后戮之无赦。然此非为其人惜也,所以重朝廷之名器也。如此则为大臣者,必皆知所以自重,竭力效忠,以酬千载之遇矣。 四曰选良将。 近年以来,在京在外总兵者,或以外戚至亲,或以内官姻党,或以贿赂而得,或以奔竞而进,率多庸碌鄙夫,粗鲁悍卒,不识韬略,罔知筹算。在内者训练无法,在外者守备无方,卖放军士,办纳月钱,差占军丁应当私役。致使士卒内怨,夷狄外侵,皆由将不得人之所致也。 然选举将官皆由兵部。今兵部尚书马昂,庸才下品,素不知书,怙宠恃思,矜已傲物,既无素定之策,又无应变之才。方且拓贤嫉能,张威作福,边方奏请者,则不问言之当否,而妄行参驳,使巡抚等官不得行其职。出征报捷者,则不审功之有无,而妄奏升赏,使冒报功次者得以售其奸。至于总兵缺官,正当广询博访,豫求真才,顾乃任情徇私,苟且塞责。致使仗钺者多驽骀之才,搴旗者乏熊罴之士,猝有警急,委任何人? 伏望先将马昂黜退,别选忠良以充是任,俾兵部得人,则总兵者皆得其人。总兵得人,则战胜守固,而朝廷无回顾之忧矣。 五曰保全内臣。 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内臣者。内臣出入左右,能勤谨顺承,奉迎意旨,多为人君之所亲爱,遂委以国政,授以大权,操舍与之询谋,刑赏任其憎爱,致使坏乱大事,几败国家,然后治以重刑,戮于市朝。远览赵高、李辅国之徒,近观王振、曹吉祥之辈,皆始爱之,而终杀之,非所以为保全之道也。 今之内臣有管军者,则私役军丁。管匠者,则私役人匠,放闲在外,办纳月钱。乃其事迹发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一也。 又有起造房屋,置立田产,乃无籍之徒投为义男家人,或总兵等官,送与小厮伴当,俱各悬带匠人牌面出入内府,在外则假借声势,放肆百端,虐害小民,甚[至]有不轨如曹钦者。及其事迹发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二者。 其在京文武官员、僧道人等,多与之交结。甚[至]有无耻大臣,或行叩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内臣因而嘱托,鬻狱卖官,擅作威福。及其事迹发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三也。 伏望悉遵太祖旧制,今后内臣不许在外管军管匠,亦不许置立田产房屋。其家人义男,悉令所司究其来历,发回原籍当差。亦不许文武官员、僧道人等,与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无内外,政无大小,悉断自宸衷,及与馆阁大臣计议,不可使内臣得与其谋。然此非欲疏之也,正欲保全之耳。至于侍奉左右,亦惟择谨厚者为之,厚其赏责,使之丰足有余,无复外望。如此,非惟天下睹清明之政,蒙至治之泽,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无诛夷之患矣。保全内臣之道,岂有加于此哉! 渊字志默,绍兴之山阴人。后复与同官王徽等疏论太监牛玉,因极言内臣与政之害,谪四川茂州判官。(王渊,《明史》有传) …… 成化间,无锡杨璇巡抚荆襄,恐流民为变累己,因为危言以动朝廷。诏遣大臣往察其变。自巡按御史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璇议,遂迁发诸流民还其故土。 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孙矣,官司迫遣上道。时夏月酷热,民皆聚于舟中,不能宿处,气相蒸郁,疫病大作,死者不可胜纪。弃尸水道,塞碍舟揖,哀号之声动天地。 时有作《大明平荆襄碑》以纪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坠泪碑。”问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为之泣;今以虐政毒民,而民亦为之泣。其坠泪虽同,而情则异矣。 其后杨璇坠马得疾死,御史薛承学病疽死,守巡官以下,一时死者数人。论者谓天实诛之也。 呜呼!重富贵而轻民命者,盍亦知所戒哉! 成化十三年,浙江镇守太监李义、巡按御史吕钟各奏,据绍兴府山阴县民夏瑄状告称: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时,有本村杨广兄弟,令其家佣工夏全驾船来家,邀瑄弟夏珪饮酒,坐待于门。忽见门外有鲜血如雨点,射着夏全脚上及门壁,不知所从来。阶下积血约高尺许,时有十人走集看之,俱被血溅污衣。既而杨广等下船归家,血亦随人直至水滨。其人以蓑笠置船上,被雨冲湿,亦有红色如血。次日,但见船中有血,凝定可斗余,人皆惊异。 时礼官复奏,以所在灾异叠见,请遣官祭祷岳镇海渎诸神。诏从之。 臣冠私议曰:血者,阴属也。班史《五行志》谓之赤眚赤祥。汉惠帝时雨血于宜阳,刘向以为诸吕用事之应。京房《易传》曰:“佞人禄,功臣僇,天雨血。”是后妖人王臣依附貂珰,所至刮索珍玩,民间骚然。诸以左道进者,内侍梁方、韦兴,方士李孜省,髠徒继晓等,皆滥窃宠幸。已而王臣败,枭首于市,孜省等亦相继伏诛。孰谓天道谴告之不豫哉! 成化二十年岁次甲辰九月乙酉朔,越二十六日庚戌,皇帝遣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黄赐致祭于东岳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虚圣祐真应真君,定录右禁至道冲静德祐妙应真君,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应真君,惟神清虚冲澹,秉正存忠,灵妥三茅,功施社稷。朕自即位以来,二十年矣,四海奠安,万方宁谧,惟赖神之灵贶以致于斯,今特谕祭神,其不昧尚冀鉴之。 臣冠窃惟皇祖酌古准今,定为祀典,其山川称号,不过曰:“某山之神”而已。百年以来,治定功成,文日滋盛,至山之称号至于如此。又以奠安社稷之功,皆归于神,意者其时词臣著作考据益精,而万、刘诸公辅相参赞,又别有道?非愚儒所知也。 尚书三原王公恕巡抚南畿时,尝以书抵东刘阁老,其词云: “某薰沐再拜太保尚书学士寿光先生阁下,辱赐诗,奖与太过,感愧无已。仆岂好为此哉,诚以责任在己,不得已也。 夫公孤任天下之责者也,巡抚任一方之责者也。任天下之责者,天下之休戚不可以不言,任一方之责者,一方之休戚不可以不言。公孤居天子之左右,于其事之初,皆得而可否之。可者将顺之,不可者救正之。是以天下阴受其福而不知其功。巡抚处千里之远,有所言,非奏疏则不能达,言非切直则不能尽其情,是以逆耳而难入,无益于成败,得罪于左右者多矣。 当今天下一统,如金瓯之完,无纤毫之缺,诚能以仁义道德为城郭以居之,立纲纪法度为甲兵以守之,使人不得而窥瞰,物不得而搏击,则斯器可以千万世为国家之所有。若置之通衢之中,无城郭以居之,无甲兵以守之,使人得瞰之,物得搏击之,万一有损,不能无费大匠陶熔之力矣。近观时政,如置新器于通衢而不之顾也,仆窃为国家忧之。是以言之至再至三。即不见从,又不得去,而徒为是凛凛也。声名之有无,岂暇计哉! 执事为国家之元老,居论道经邦之地,苟以嘉谟嘉猷入而言之于内,出而顺之于外,使国家置斯器于安,固保斯器于无穷,其功岂不伟哉!保之之道无他,惟在乎节用爱人,进贤退不肖而已。噫!非执事不敢为此言,亦非执事不能容此言,惟察其愚而恕之。幸甚。” 成化末年,中外争进奇玩以邀恩泽,倖门大开,爵赏狠滥。又广营寺观,帮藏虚竭,内阁诸大臣无一言正救。独王公连上疏谏诤,寿光盖作诗以誉公,实则讽其言之太直,欲使缄默,与己同流,不至于泾以渭浊耳。公复以此书,词直气昌,略无畏沮之意。其未云“节用爱人,进贤退不肖”,在当时尤膏盲之箴贬也。 宪庙时,德王之国,欲迎养母妃,疏请于上。诏报曰:“汝母即朕母,朕养即汝养。汝以一国养,孰若朕以天下养。”王遂不敢复请。 一时中外传诵,无不称叹。盖数言之间,上不违祖宗家法,中不失天子之孝,下不伤兄弟之情。而其词温厚简当,得王言之体,可以为万世法矣。 安成彭公礼巡抚南畿时,命苏郡立周、夏二尚书祠于胥门之西岸,岁时祀之。周则文襄公忱,夏则忠靖公原吉。后有人题诗于胥口之伍相庙云:“周、况曾蠲百万租,二公遗爱在三吴。乡人近日祀冯道,为问将军合义无。”盖指忠靖也。(原注:忠靖先事建文朝,故有冯道之目)殊不知三吴减额之议,实由忠靖发端,周、况二公特收其成功耳。以此而血食于吴土,固宜,不暇论其他也。吾苏陆全卿为御史时,尝亲见户部旧牍中减粮额事,因知皆本于忠靖云。 卷二 胡穆仲,婺之永康人也。至元中,与弟汲仲并寓于杭。穆仲尝风雪高卧,午不启户。道士黄松瀑悯其清苦,言于真人杜南谷,南谷馈以酒米薪炭,皆不受。赵文敏尝求汲仲撰罗司徒父墓铭,赠遗甚厚。汲仲曰:“吾不能为宦官父作铭,请辞。”时绝粮已一日矣。 予观世有通显而贪昧者,不问人之贤愚,但视其赠遗之厚,则为之作铭诔表传或庆贺赠送之文。又有为郡县者,欲货取津要而无从,乃假求修庙学碑或刻书序,因以纳贿。与者意在求人之庇己,受者意在掩己之苟得,各自以为有术也,不知明者视之若掩耳盗铃,何益哉!闻汲仲之风,亦少知愧矣。 黄乾亨,闽之莆田人,成化乙未进士,授行人,与给事中林荣俱奉使满刺加。渡海,舟复,二使及舟中之人咸溺焉。 凡海舶必以小舸自随,下碇登陆,非此不可。时有数人附舸随流,至一岛。众皆馁,无所得食,其中黠者相与扣石出火,聚岩下枯翳燃之,使烟浮于空。并海逻戍望见之,意其寇也,来迹捕之。问知其由,因载以返。 初,乾亨将行,祈梦于九仙山。神告曰:“飞龙亭下过,方始问前程。”出海经一所,忽见亭中匾“飞龙”二字,行未远而没。信知人之死生有定数也。 武功伯天全先生徐公,博学,无所不通,尤好相地,每自神其术,以为郭景纯复生。按察副使冯士定父丧,将卜葬,求先生相地。历吴中诸山殆遍,罔有惬意者。既而得一地葬之,以为最吉。后士定起复至京,自投宗人府井中死,吉安在乎? 又,武功之婿蒋廷贵将葬其祖,发引之日,亲宾填门。先生谓其地不吉,遂不克葬。复择地,逾时而始葬,曰:“此地必出魁元。”己而廷贵果中南畿辛卯经魁、戊戌进士,人皆诧先生之术验矣。不三年,而廷贵以乐亭令卒于官,遗腹一子曰焘,至十七而夭,吉又安在乎? 大抵地理之说,不可谓尽无,但吉凶祸福,则岂必系乎此。昔罗大经云:“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荫。夫人之生,贫富贵贱禀赋已定,岂家中枯骨所能精移乎?如璞之说,是上天之命反制于一杯之土也。”杨诚斋亦云:“郭璞精于风水,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孙。然璞不免刑戮,子孙卒以衰微,是其术已不验于身矣。后世方且诵其遗书而尊信之,不已误乎!”伟哉,二公之论,足以破世俗之惑矣。 昆山张副使节之,吵一目。尝游虎丘寺,见千眼观音像,戏题曰:“佛有千眼,光明皎皎。我有两目,一目已眇。多者太多,少者太少。”一时传为雅谑。 成化间,巨珰黄赐丧母,有词臣衰绖持杖而哭焉,以孝子自处,为言官所论。 予尝读史云:北齐和士开母丧,附托者咸往奔哭。富商丁邹、严兴,并为义孝。有一朝士,号哭甚哀。乃知古亦有是矣。 呜呼,义孝之士,千载复见,亦云异哉。 天顺间,琼台邢公宥守苏时,岁侵民饥,公具疏闻于朝,乞行赈贷。都御史韩公雍时家居,语之曰:“公必须极可而后行,民已为沟中瘠矣。旦擅发之罪不过收赎,以数斛赎米而活百万生灵,何惮而不为哉!”语未毕,邢公大悟,即日发官廪以赡民,所全活者甚众。 尝读晋史《外戚传》,王蕴为吴兴太守,郡饥,蕴开仓赡恤,主簿执谏请先表上待报。蕴曰:“百姓嗷然,道路饥馑,若表上须报,何以救将死之命乎。专辄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义而败,无所恨也。”于是大赈贷,赖蕴全活者十七八焉。后蕴于太元九年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太平之世,人皆志于富贵,位卑者所求益劳,位高者所得愈广。然以利固位,终不能保其所有。故时人为之语曰:“知县是扫帚,太守是拼斗,布政是叉口,都将去京里抖。”语虽粗鄙,而切中时弊云。 成化丁酉(十三年,),山西石州有男子曰桑冲,美姿貌,伪为妇人饰,善刺绣烹饪。出入人家,女妇与同处者,多为所污。 至真定,一士人延冲于家。其婿欲私焉,夜往强拥之就榻,其奸始露。执送于县,讯之,具得其实。械送京师,磔于市。 (成化)时,又有男子诈为宦者,至闽中,藩臬二司皆伏谒,宦者不为礼。福守唐珣独觉其伪,私戒馆人入内觇之。数日,馆人已熟察其状,乘间仆之地,探其胯下,则男子也。二司官初骇珣之所为,已而大惭服。械至京,以尝在中贵汪直门下,释不问弘治间,京师有少妇,出城一舍许归宁父母。明日侵晨,抱哺一儿骑而入城,道遇一僧控其马,令之下。妇拔一钗与之,冀释己。僧曰:“但欲汝下,不须物也。”妇知其意,乃出怀中儿与之,曰:“第持此,伺吾下。”僧方抱儿,妇亟跃马去不顾。僧手裂儿为二。妇行里许,见行道数人,驻马谓之曰:“前去一僧,盗也,行劫我,赖马壮得脱。持我儿去,汝辈可救之,当重赏汝。我京中某家妇也。”众前追及之,果见儿死道上,僧方就水旁浣衣上血。众执送官,论死。 呜呼!怜爱儿者,妇人之情也。此妇独割其至爱以全节,亦烈矣。独失其姓名为可恨耳。 寒月有三人渡钱塘江,覆舟溺水,既而皆登陆。一人忍寒至酒肆中,食汤饼且饮酒,独无恙。二人急入浴室中求浴,越明日,俱死。 盖寒入腠理未深,内食热物,故生。外用热汤沃之,则逼寒气入内,故死。此正与旧说三人雾中行者相类,故录以戒后人。 卷三 苏长公书《醉翁亭记》真迹,在绍兴小儿医方氏家,后为士人白麟摹写赝本以售于人,见者不能辨,往往厚值市之。或以一本献工部侍郎王佑,佑奇之,自云家藏旧物,以夸视翰林诸老。方共唶唶叹赏。学士王英最后至,熟视之,曰:“艺至此,自出其名可矣,何必假人哉!”众愕然,问其说。英曰:“宋纸于明处望之,无帘痕。此纸有帘痕,知其非宋物也。”众方叹服其博识。 陈暹季昭为南京刑部郎时,见司务分俸钱独少,其人色颇不怡。季昭戏赠一绝曰:“俸钱三百意如何,日计虽廉岁计多。内帑莫言成贯朽,皇家涓滴是思波。” 杜宏,字渊之,河南临颖人,弘治庚戌(三年)进士。为阜城令时,北方常有群盗共谋杀人以诬人求贿。(原注:此人谓之“贩苦恼子”,又曰“打清水网”。)杜令廉知其事。 会有数商人来邑中,与人交易而斗。明日,其徒一人死逆旅中。令遗坊甲追捕。顷之,一人至庭,牵二骏马,鞍勒皆饰以银。 出符以示令,指符中姓名曰:“张鉴即我,张庆即今死者,吾弟也。我张都御史从子,鬻鹾淮上,索逋直来此。昨令吾弟出外,以黄金易钱,与人斗而死耳。”令使人捡其橐,有新衣数事。诘其余资安在,曰:“吾所挟银,途中遇盗劫去矣。”令笑曰:“汝诈也,银且被劫,安得黄金独存,又余美衣骏马耶!”其人词穷色动,欲逸。令乃絷其马,封其橐,使卒守之。 适景州逸他盗,逻者获一人,自言:“我商也,有同侣在阜城,与人斗而死,我避官府来此耳。”州吏移之至阜验之。 令得之甚喜,乃移景州,并逮其人至,严刑讯之,盗皆具伏,曰:“某实杀人求贿者,于某地杀某,于某地又杀某,计凡杀九人。今死者非吾弟也,乃途中行焉者。吾衣食之,令饲马,复令其与人交易而斗,乃杀之耳。”令犹恐有遗情,复再三汛之。中一人杨杰吐实曰:“初与交易者斗,乃杰也,非死者也。杰等五人于此夜杀饲马者。杰恐斗者识我,即逃往景州耳。” 令乃具白巡抚大臣,下属郡核盗所陈往事,皆符合,遂闻于上。内批:“为首者凌迟处死。为从者斩,枭首示众。仍著为令。”远近称快。 后杜令以内艰去,服阙补山阴,召为监察御史。 成化间,牟俸为江西按察使,夜梦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而咆哮。噩而悟,意殊不乐,明日以告僚佐。有胡佥事者,颇廉明,知牟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狱得无有冤乎?”牟艴言曰:“吾有冤狱,汝何不纠之?”胡唯唯而退。既而闻牟尝断吉安一女子杀夫事有疑。 初,女子许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贫,女家恒周给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学友周彪。彪家亦富,尝闻其女美而欲求婚。 后贫士亲迎时,彪与偕行,谚谓之伴郎。途中贫士遇盗杀死,从行者惊散。贫士之父疑女家疾其贫而杀之,冀欲他适也,遂讼于牟。牟乘怒不察,因按女有奸而谋杀其夫,盖恶其家之不义,故被以污名耳。 胡移文逮贫士之父问之,具得其颠末。但问女与何人奸,则不得其主名。使媪验其女,又处子。乃谓贫士之父曰:“尔子与谁交最密?”曰:“惟周彪耳。”胡沉思曰:“虎带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牟之梦是矣。” 越数日,移檄下吉安,取高才生修郡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既至,觞之。酒半,独召彪于后室,屏去左右,引其手叹曰:“牟公廉知若事,欲置若干极典。吾怜若才,且劝牟公以狱既成,不容反异。若当吐实勿欺吾,则相救耳。”彪错愕战怵,即跪,悉陈之。 胡录其词,潜令人擒其同谋者,具狱以白牟。牟即日欲杖杀彪。胡止之曰:“须众证以出其女,然后杀之未晚也。不然恐有异词。”牟愧谢,从之。一郡称胡为神明焉。 邢部郎中李玺,成都人,在京娶一妾,极妬悍。玺目忽不能见其妻,若病盲然。僚友闻而怪之,共诣其家,掘地得木人,用针刺其目,去之,玺目复明。 乡人顾参政天锡云,为刑部郎时,亦曾鞠一事。有千户娶妾后,与其妻如仇,不欲相见。妻族疑其妾之咒诅也,讼于官。天锡召千户讯之,千户亦不讳,但云我亦不知何故,见妻则仇恶之,不欲视其面。乃盛陈狱具以恐其妾,妾辞不知,曰:“恐是吾母所为。”即引其母讯之。母具吐实云:“在千户家土炕及卧褥中。”令人发之,果得小木人二枚,相背,用发缠之。裂其褥,中置纸金银钱,面幕相背,复有彩线及丝连络其间,不知何术也。遂论置于法。而千户与妻欢好如故。 …… 顾天锡为刑部郎中,奉玺书录囚山西。时大同天城卫刘千户之子安,娶于指挥之女,有殊色,出则人皆属目焉。安性豪荡不检,一日与弟富从外醉归,其弟语安曰:“吾嫂与木工王文美通。”安闻之愤怒,抵家,见于熟睡,即解佩刀截其首。复至王所,并取其首。明旦,诣巡按御史以二首献。 巡按以委属吏讯鞠,终不明,仅拟安以罪人已就拘执而擅杀者绞。累经刑官审录,不决。 天锡至,用意询访,亦不得其实,即草奏,欲以疑狱请谳;又欲奏请驳行巡按御史再问。其词略云:王文美、于氏,既非奸所捕获,亦非罪人已就拘执。只因兄弟乘醉之言,一时戕害二命,实力非辜云云。天锡已具二稿,意尚未定。 是夕三鼓,梦一妇以发蒙面,于马首称冤。遂惊寤,毛发棘竖。至明,召藩臬守巡官皆会,即依后驳稿为奏上之。 呜呼!观此则治狱者其无以民命为可忽,以幽冥为易欺,而徇情上下其手哉! 绍兴一妇,为所私者杀其夫。事觉,妇虽不知情,准律当绞。分巡金事某,恶其淫荡而贻祸于夫,遂坐以知情律。狱成,剐于市。 是后,佥事所至,夜辄有鬼随而称屈,或抛击砖石,或寐中被其曳掷床下。乃问曰:“尔鬼何冤?当明以告我。”空中忽语曰:“我某妇人也,我罪只当绞,尔何置我于极典邪?”佥事曰:“坐尔极典我实为过,然尔亦不过一死。况我非私意杀尔,尔何为者!”叱之去,后鬼乃不至。 嗟乎!绞与极刑,均之死也。况此妇淫荡,以致死其夫,可谓微贱如虫鼠者矣,然犹有灵如此。彼酷吏滥杀无辜,独无报耶! 无锡华允昭常畜一鬼,工象齿,葫芦大如龙眼,中藏杂器数十事,皆象齿所造,微细不可数。用黑角小盆一枚,如当三钱大,然后倾葫芦中物于内,则黑白分明。盘上有字曰某年某月某人造,字皆隐起,其大仅如芝麻,非少年明目之人不能读。中有浮图一,长如粒米,亦有七级,每级就上斫一环束之。一水桶,上有连环作铁索状,每环固转相交,如麻粒大。其他如剪刀、琴、琶、烛台、镜奁、炉、瓶之类,悉如麻粒,而规制俨然。人玩时,鼻息稍粗,则触而飞起。一象齿杖,上刻鹤喙,凡物重叠不分,则以此挺拨之。 韩非子言,燕王集巧士,有自言能以棘刺之端造沐猴者。今观此,则此技信有之邪! 苏人诸役之害,无如驿传、马头、借债为甚。其始自永乐间。文皇帝以北方民买马当役艰难,暂令南方百姓代之,三年而复。故其后因循不改,至今百余年。南人非土著,不谙马性,皆转雇土人代役,马死,则为之买以偿官。驿吏及代役者,规买马之利,多盗减刍粟,马日赢饿死,所费不货,于是称贷以继之。山东诸处民之狡猾无赖者,立券取数倍之息,先以贿结津要,约追得所负,则以其半奉之。故贪墨者争为作书抵郡邑,每县动以万数。守令望风督责,民破产以偿,无所控诉。 翻阳贺公霖守郡时,有都御史边某者,先下札郡县,云:“子弟皆居家读书务农,并无出外经商放债者,如有假托干扰,所在官司即捕执送京治罪。”既乃以手书取债,令子侄赍诣有司,其为计亦狡矣。贺公悉力与追,民不胜捶楚,如伪卷偿之。未几,贺公卒于郡而无子,边公亦竟以贪罢云。 夫居台省者,当兴利除害以报国。任专城者,当奉公守法以惠民。今也,反之,斯获罪于天甚矣。其及此也宜哉。 弘治壬戌(十五年,)以后,人帽顶皆平而圆,如一小镜。靴、履之首皆匾如站鱼喙,富家子弟无一不然。云自京师倡始,流布四方。衣下壁积几至脐上,去领不远。所在不约而同,近服妖也。 山东鲁桥,相传有灵哥者,乃老猴精也。云能知人祸福及未来事。 弘治壬子(五年,),予以岁贡上京,与二友同往。先有一妇人出迎,问予三人出处,盖饴之也。诡言今日大圣出游不在,方遣人迎之来矣。须臾,顾左右如有所言,闻壁间索然有声,又有声鵙鵙,若鸣鼠,然妇人自能辩其语云云。其物盖灵哥所役使,妇使往迎之也。 已而灵哥来,止室中床上。床有帷,帷外又设幕。妇人先入幕中坐,若为神所依者。帷中忽作声,俨如老人,警咳其言,无绝殊者,亦不能如未来事,不过甘言求索耳。 及去时,则空中隐隐如鸽铃声。然盖所传灵异者,皆妄言也。 《史记》言:汉武致神君,闻其言不见其人,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言行下与灵哥之事绝相似。传云:妖由人兴,谓此类也夫! …… 卷四 …… 吴节,眉州人,景泰甲戌(五年,)进士,历知岳州府。岳有盗亡命,其妇坐系,有娠当娩身。节命于狱户外设苇箔蔽风,使蓐媪视之。己而妇以产难死。节出俸资,命狱吏买棺付其家人瘗之。 后岳州江中盗起,势甚猖獗,藩臬以闻于朝,诏命府卫合兵讨之,兵甲犀利,士卒精悍,自谓贼不足灭。不意陷入贼伏中,悉为所戕,无脱者。贼中一人忽大呼曰:“恩主吴太守安在?”已而登舟,见节叩头,自言姓名,则前瘗妇之夫也。亲护节登陆,舟中之人皆得全。节后仕至都御史。 呜呼!节之加恩贼妇,亦古罪人不孥之意,初无心于望报也。特以一念之仁,终险危而获济,岂可谓非天道哉。然以盗之不道,犹知感恩而不忘报如此。莫强如人心,而可以仁结,讵不信夫! …… 沈洪济,乌程人,有姊入宫为女官。 洪济登乡荐,小录进御,其姊见洪济之名,作诗寄之,曰:“一自承恩入帝畿,难将寸草答春晖。朝随御辇趋青琐,夕奉纶音侍禁闱。银烛烧残空有泪,玉钗敲断恨无归。年来喜子登金榜,同补山龙上衮衣。”一时多传诵之。 郡邑城隍之神,当用木主。今为土木之偶,被以衣冠,又求一入以实之,且立后殿,设像为夫人。世俗可笑事大率类此。 附城之邑,令长初莅任祭祀,或旱潦祈祷,皆当就郡祠行礼。今往往别立祠,亦非也。 绍兴府城隍神,初设土偶,尝为太守白玉撤去。后有通判于某,贪鄙无识,乃复设像,更立六曹,若郡邑官府之制。其年朝觐幸不黜免,遂自谓神庇。后竟以贿败。而土偶至今承讹,莫有能去之者。 会稽山神词,建自隋开皇十四年,累代加封王爵,本朝只称南镇会稽山之神。予分教绍兴日,尝陪祀至祠下。其地两山分脉,自南而北。两水夹流,至祠下而合。祠南面山,山巅香炉一峰,正对祠门。其正殿中有石筍一支,高可丈许,后人从其上加土为衣冠之像。闻故老云:石筍疑有所长,土像项下时并裂,岁加修葺,既而复然。郡守岭南彭公谊,命塑工设像多空其中,乃得不坏。 彭公固贤守,有方略,惜其未明鬼神之情状耳,盖石筍乃山之灵气所钟,故前人于其处建祠。今妄加土偶,只以渎之,又建后殿设夫人像,不知当以何山为妇而作配乎! 考之洪武礼制,祭社稷仪式云:神牌二,以木为之。至岳镇海渎帝王陵庙下,则云:其牲物祭器仪注,并与社稷同。此其当设主而不为像,貌亦明矣。 我高皇帝厘正祀典,实万世所当遵守。有民社者,于此类宜亟正之,不可安于陋习而不反诸经也。 正统间,有谭禧者,为绍兴府推官。会修庙学,禧见大成殿材皆良木,乃以他木易之作器。又铸新铜爵易古爵。后禧罢官,过大庾岭,为盗所杀,人以为圣人之灵阴加谴罚也。 予曰:禧为人好贿,既挟厚货,慢藏诲盗,故取杀身之祸。圣人在天之灵固无不在,岂若是之屑耶!然亦足以为贪昧无礼者之戒矣。 成化丁未(二十三年,),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溪港皆不通舟揖。先是嘉兴诸邑船尾率画锄钁之属,不约而同,莫知所起。意者水道枯涸,藉此器以疏浚,此其兆之先见者欤! …… 卷五 成化间,湖广旱,襄王欲得祈雨者。或云黄州有人善此术,王使召之。其人与三人俱来,入山,遍求龙,见一石上有青绿晕,曰:“此有龙矣,恨老。”乃以锥抉石上,果有一穴。久之,穴渐大,复以一竹筒探入穴口,穴中水随溢出。须臾云气四合,雷电交作,风雨骤至。其人以瓶罂负石穴中水入城,雨方可五里许,城中皆遍,惜所及不广。其人云:某处有龙年少,可多得雨。王恐龙怒,致水患难制,遂厚赐其人而遣之。 吾苏夏御史玑知大庾县时,岁旱,邑人云:大庾岭下有龙湫,祈则有雨,但山谷深险不可入。昔有主簿往祈,以绳缒入,雨骤至,从者或溺死,自后人不敢入。 夏公从数人以往,以索自缒下,出则令从者先登,复以索援引而上。其地有水洞,方可半里许。水皆玄色,沸涌流出溪涧。古木大可数抱,蔽翳天日,山箐深密,幽僻可怖。以器绕水求龙,但得一生物,则龙至矣。或虾、或鱼、或蜥蝎之类,得则疾出,仍以笔志岩下一小石。得雨后,乃令人送龙至故处,而取石以为信。否则人从中道弃龙,不至故处,后祈雨则龙不应矣。夏公为人诚笃,龙出,雨降,送之,一如故事云。 张士诚据姑苏日,开宾贤馆廷纳诸名士。慕杨廉夫名,欲致之不可得。闻其往来昆山顾阿瑛家,潜令人伺人于道中,强要之。 既至,适元主遣使以上尊酒赐士诚。士诚设宴以飨使者,廉夫与焉。即席赋诗云:“江南处处峰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 士诚得诗,甚惭。既而廉夫辞去,士诚亦不复留也。 “介马驮驮百里程,青枫后夜血书成。只应刘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汉水清。”此杨廉夫《题临海王节妇》诗也。宋亡,节妇被元兵掳至嵊县青枫岭,啮指血题诗石上,投崖死。廉夫责其不即死,故诗云云。 尝闻故老言:廉夫无子,一夕,梦一妇人谓曰:“尔知所以无后乎?”曰:“不知。”妇人曰:“尔忆题王节妇诗乎?尔虽不能坏节妇之名,而心则伤于刻薄。毁谤节义,其罪至重,故天绝尔后。”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诗曰:“天荒地老妾随兵,天地无情妾有情。指血啮开霞峤赤,苔痕化作雪江清。愿随湘瑟声中死,不逐胡笳拍里生。三月子规啼断血,秋风无泪写哀铭。”视前诗,予夺大不相侔矣。 梦之有无不可知,予考宋景濂作廉夫墓铭,有一子一孙,则无后之说亦非也。或别一人尔?夫士君子论事,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节妇被掳欲死,而无便可乘,迨临险而后行其志,既杀身以全节,则他非所论矣。廉夫之评,诚过刻哉! …… 邓卿,字志夔,蜀人,为户部主事。妻甚悍戾,尝捶楚婢妾,足指皆坠,弃粪草中,家人畚出开道上。邻家儿以线系足指,曳竿上引鸱鸟,为西厂逻卒所执,间所从得,儿指示邓处,卒以闻。诏下锦衣狱讯鞫,具得其实,卿坐削籍为民。 今世淫祠如观音堂、真武庙、关王庙、文昌祠之类,皆愚夫细人所为。至于迎神赛会,渎礼不经之举,非但糜费民财,亦奸盗所由起。为世道虑者,力加禁遏可也。顾今之从政者,于此等事多阔略不省。间有愚懦不学之徒,怵于祸福之说,反从而助之。故邪妄之习日新月盛,可为叹息。 大抵建祠赛会,必有首事之人,乘时渔猎民财。宜痛惩以法,没其所敛之物于官司,以备赈济之用;取土木之像投诸水火,而以应祀神祗或名宦乡贤神位改奉于中,以塞其妄源,则祷张为幻之人,知警畏而自息矣。 天台陈公选督学南畿学政,凡学校中有文昌祠像,皆移檄郡县撤毁之。公去后,有谄读以冀非望者,稍稍复之。长洲邑学有生徒,复舍财塑像,庄严逾于昔。后其人病疽死,亦竟无闻于科目云。 …… 故事,每秋后于阙下录囚,公卿咸在。一岁,汛及一劫盗。盗抗声曰:“若辈何必问吾,吾为贫,故行盗耳。若辈位高禄厚,非贫也,罔不贪黩货贿,较诸白昼劫夺者为甚,尚不知愧乎?”诸公无以应。事在成化间。 时新昌俞公钦为礼部侍郎在列,尝为人言之。此颇与岳氏《桯史》中郑广诗相类。 …… 仕宦者至京师,赂遗津要,或有厚薄,津要之人报之亦不同。故京师语曰:“十两银,到处寻。一匹缎,看一半。一匹纱,没处查。” 辇毂之下,民物繁众,而风俗之浇薄为甚。会城大府亦然。古者取士于田野,管子曰: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呢,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人能力田务本,置身山林之间,非惟足以养心畜德,至其子孙,亦自有朴雅之风,为学亦深潜缜密,与寻常市井入不同。出而仕宦,必多风节清介之士。立家业为子孙谋者,盍亦择所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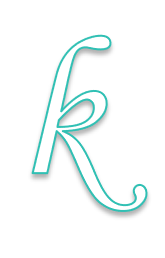 下旋
下旋 左旋
左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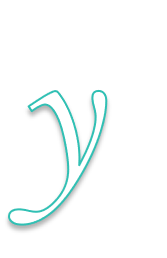 上旋
上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