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真經集註雜說 經名: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宋彭耜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直經集註雜說卷上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一爾。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種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旦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釆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其師傳授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並《纂微篇·序》,《道藏目錄》。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懽、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六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唐太宗謂傅奕日: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日:佛是胡中桀點,初正西域,漸流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玄言,文飾之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汝等勿學也。見《舊唐書》本傳。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結庵河渚間,守令謁者,辭以瘖。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云。見王績《仲長先生傳》及文中子注。 東皋子王績,字無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有田在河渚間,仲長子光結廬北渚,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宇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褘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箚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書少異,故並錄之。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楊雄傳》 阮藉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弼注《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老子所作。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一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平叔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見《世說》並注。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緣。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已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眾皆為之屈。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見《新舊唐書·儒學傳》。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啟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宗聞汴水輩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見《國朝事實》。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無為之術,臣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漢文,今摭其說十數篇錄于後。 漢文即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於社稷為先,以有德於我身為後,此所謂後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釆之,未嘗不稱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善,此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善也。 漢文初登虎圈,嗇夫口對無窮,拜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陛下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敗亂,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蓋知辯者不善而多言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除之。故賈誼上書至於引廟謚為言,而文帝嘉納,可謂無忌諱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彌貧。 孝文為尉它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以寵之,尉它於是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為帝,此即強之弱之,與之奪之,在我而已矣。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蓋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袁盎卻慎夫人坐,文帝改怒為喜,厚賞袁盎,可謂自勝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之所以強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勝者張。 文帝納賈誼譏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助無為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玆乎。 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為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為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有為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聞陰訐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訐之路,拒而不受,聖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通判並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居儲貳。臣曰:唐中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為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疏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得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並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桁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並見本集。 穎濱蘇文定公曰: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見《道德經解》後序。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而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見經注。又曰: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遊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夫豈其所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壓之差,或致千里。見《樂城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為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啟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為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為老子,詳而為列子,又其詳為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語錄》。 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口國氏雜錄》。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榮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見呂氏《師友雜志》。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書云: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眄眄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溫公自號迂叟,嘗著書曰《迂書》,內老釋一章云: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又云: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並見溫公《傳家集》。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播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五口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仁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閣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琥,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並見本集。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夭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見《眉山集》。 張右史末《老子義》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斷,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張堅序曰:至柔教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真氣應之,玆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真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為止觀,司馬子微得之而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 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侍,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為尤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見本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那,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日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己,此其所以不同也。並見《淮海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立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范忠文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陽相與之際,文簡而理備。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肺。見《耄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稿》。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註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九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李昭玘曰:鬼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適中爾。見《欒靜先生集》。 西臺畢仲辦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為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眉山蘇籀,穎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註,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卷上竟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卷下 宋鶴林彭耜纂集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為大聖祖,聖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註《老子》並《義疏》於天下。又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見《新唐書·藝文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冊寶,己酉,朝謁太清宮,見《九廟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逼無為,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莊子釋文》三卷,欲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國朝會要》。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兖州孫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豈天下太平乎。明皇僅得歸闕,復為輔國劫遷,卒以餒死,山豆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見《九朝通略》。 方臘亂浙右,聲搖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人,至束宮太子問焉,振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調繆牖戶而已。老子亦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也。見《九朝通略》並《東都事略》本傳。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為比部員外郎,因奏對乞解易箚子,略曰:共惟陛下天縱睿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為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宸衷,為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眾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連沙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輻,至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長生躡白雲。並見《梁谿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說,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並見程氏遺書。 胡文定公安國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之說,亦皆至論也。見《語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保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鄉集》。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 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歟。見本集《觀物篇》。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過。見《邵氏聞見錄》。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為古今論仁最有妙理。見邵博《聞見後錄》,謝氏《語錄》亦載。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嘆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為不肖,然則欲為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為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眾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為不足為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肖則不足以為道也。又曰:老子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淈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宴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曏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曏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懦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以上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于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我於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裹。並見經註。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謂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故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言》。 北山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又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為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后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死地哉?又曰:眾人之見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戕性,取舍滑心,眾人之過也。眾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遣之也易。以覺為礙,以解為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為病顯,以法為病微,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元覽,蓋謂是也。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為解縛。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為覺礙。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祟厲之為哉?又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為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己愈有,與人己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並見《北山集》。 栟櫚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黃帝,其道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真可駭者。其為家三十有七,其為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絕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張良為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為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靜恭儉無為,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流滋蔓,變怪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見《栟櫚集》 嚴谷山人江裹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御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概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為喻,夫湖海之涵浸,與拗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勒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詛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玆所以為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睹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睹耶。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御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件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御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御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默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御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問身》。又曰:或問何者為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御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陶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氏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毋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綠,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袤,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楊文安公樁,紹興間以從橐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任聰明,役智力,是弊精神於寡淺者之所為,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吝,不敢為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妙,渾然天成,物之來干我者,初無容心,隨所遇而應之。我無忮心故能慈,我無欲心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為天下先。其所以日用者簡易至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所能成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大《易》老氏之言若合符節,帝不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不伐,不競不絿,非不敢為天下先耶。下至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如文帝幾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幾於不敢為天下先,是則有天下者寶其慈且勇,寶其儉且廣,寶其後且先,雖二帝三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進也。又曰:道家者流,其來最遠,爰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御寇蒙莊之徒和其說。逮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其道以虛無自然為宗,以清靜澹泊為事,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即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傅毅以為西方之聖人,遣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是佛法始流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律,殆與六經相表裹,非若冰炭枘鑿之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老云者,吁可怪哉。並見《芸室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為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割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為漢文帝,蓋其為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樸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釆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為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為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為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為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損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誨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為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騰厭等事耶。恭蒙聖諭以某言為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又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誚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為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見《易老通言》。 沈莊仲問晦庵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其傲,是如何。文公曰:微是邊檄,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文公曰:玄只是探遠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眾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曰:此便是老子裹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 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卻不恁地。莊仲曰:卻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卻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卻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卻較虛,走了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他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冲嗇不肯役精神,又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為,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筒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污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序以道觀道等說,果為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裹。 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 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卻不會去理會。文公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口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以上並見《文公語錄》。 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見《象山集》。 苕溪劉一止行簡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己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苕溪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戅語》。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矢口而言,律筆而成書,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後人分為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序。 黃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子與《易》相為表裹,其後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有八十一首,蓋得於此。見經註。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子以仁義禮樂為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且以道心惟微,無為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日不敢為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為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絕仁棄義,禮為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為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為上也。見《經解發題》。 劉師立自號真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于右。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眾妙之門戶,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戶,如前章云眾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為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未有天地,先有元氣,是謂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張則必歙,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云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為徒,而無所爭,可以彌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己。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以德報怨之為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竅眾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註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佗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錄》。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卷下竟
 下旋
下旋 左旋
左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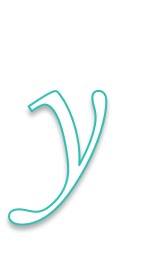 上旋
上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