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真經疏義 經名:道德真經疏義。宋江澂疏。十四卷。底本出處:《 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疏義序 恭惟聖主于帝,其訓開明道真。爰以清閒之燕,取老子《 道德經》,句為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賓貢,預太學弟子員,得以齋心滌慮,恭讀聖作。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千文,猶為道德之至。約而能散,異而能同,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甚簡,其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為之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己見,不識道真,言之迂疏。其志將以尊崇聖道,而適為抵迕。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可與明焉。恭惟皇帝陛下,得一以為天下正,抱一以為天下式,體之以見素抱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之妙,固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備,如《易》之有《 繫》,真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為不可既,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真。臣固不揆,而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為謭謭之說,而杜光庭猶著《 廣聖義》以申之,況臣久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哉。是用自央而忘其言之不逮也。 臣江澂饉序。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太學生江澂疏 徽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亙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為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為大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囿於域中,何莫由斯道也,況於人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制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則道者,人之所共由可知。道之在我之謂德。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修,不因人而致,於己取之而已矣,豈他求哉。楊子曰:德以得之。制字者以直心為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也,自得而已。則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且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所拘,新新不窮,未嘗終也。經曰:道乃久。 旦萬世而無弊者,此也。夫惟可修,故擴四端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育而充之,未嘗離也。《傳》曰:德者,性之端。充一性而常存者,此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既治,則道隆而德盛,時之末治,則道降而德衰。當周之末,大道既隱,而德又下衰,散為百家之曲說,蔽於諸子之異論,不該不徧,不全不粹,道術於是為天下裂。爰有老氏念妙道之無傳,憫生民之莫悟,以清靜為宗,以無為為本,法自然之極數,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俾誦其書者,得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其書異乎諸子而為經也。蓋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經,如經星之經,麗天而不動,如織之有經,履機而不易。謂之經焉。觀其為書,該括眾妙,廣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也。《語》 曰:默而識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德之常,非言音所能該,非淺見所能測,惟心悟神解,自得於言意之表,識之以不識,而資之深者,於是書為庶幾焉。是以聖製於首篇闡發道妙,開明士心,有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之訓也。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徽宗註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與物相去遠矣,故不可以言論。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者,為是故也。莊子載無始之言,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之謂歟?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物成數定,然後有見可名。道不囿於物,不墮於數,視之不得見也。夫孰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道不稱是已。無始又曰道不當名,此之謂歟?且天下之理,有所謂可者而不可者,已形有所謂不可者而可者,已兆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物無常宜,事無常非,事物之迭盛迭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更旺更廢,隱化而顯,顯化而隱,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昔是而今非,先迕而後合,適時之宜,過而不守,則以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雖然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雖不可言,有不道之道存焉;名雖不可名,有無名之名存焉。不道之道,所謂常道也。無名之名,所謂常名也。常之為義,以其成而不變,久而不已也。道所謂常,經言獨立不改是已。名所謂常,經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已。彼物之生必有本根,而常道常名無所本根。彼物之生本乎天地,而常道常名先天地生。雖氣有聚散,而此無去來,雖形有生滅,而此無存亡。所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得此道者上為皇,故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夫太初者,氣之始,元氣之母。得以襲之,則能遊乎太初矣,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幾是已。可以長生,故西王母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夫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道也。能體道,則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經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幾是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徽宗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疏義曰:道之至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雖欲名之不可得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命之曰道,特強名爾。此道之隱於無名者也。所謂道常無名者,以此。《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者,有形之大,而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一本於道而已,所謂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者,以此。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亦虛而已。則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雖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則萬物待天地而後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天地待道而後行。萬物資始,雖本於乾元之大,萬物資生,雖本於坤元之至,推其所以維綱一元者,果何物哉?同出於道而已。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以此。此道之顯於有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自其本宗言之,則隱於無名,斯謂之始。自其生出言之,則顯於有名,斯謂之母。言雖異而本則一也。雖然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誠能於道有見,則未有天地可得而知矣,此聖人所以後天地而知天地之始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徽宗註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玆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繳,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珠一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迺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衍於是為天下裂。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之所以為利;有極而歸無,無之所以為用。有不離無,則無實非無,無不廢有,則有亦非有。建之以常無,即不無之無也。建之以常有,即不有之有也。不無之無,無適非無,不有之有,無適非有。雖變化無窮,而其立不易,玆其所以為常也。莊子載老氏之道術言:建之以常無有。而其書首篇言之,蓋深得有無之理也。是以方其滌除萬有,雖聖智仁義猶將絕之,則不立一物,玆謂常無。及其建立萬法,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則不廢一物,玆謂常有。常無在理,未始有物,隱而難知,雖有神視,莫見其形。故其上不徼,有見於上小而妙焉。則以入乎神而小故也,故為天下之至精。常有在事,兼該眾美,顯而易見,職職陳露,匿而可為。故其下不昧,有見於下大而徼焉。則以出乎明而大故也,故為天下之至變。孔子作《易》 ,於將有為,將有行,言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則以自無適有,理則然也。於三伍以變,錯綜其數,言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則以攝有歸無,事則然也。常無常有,同出於元,至精至變,一本於神,名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有無一致,利用出入,在有亦藏,在無亦顯,曰微曰妙,特所寓爾。 惟大智觀於遠近,知有本非有,彼執之而有者,無亦寓焉。知無亦非無,彼釋之而無者,有亦在焉。惚兮恍中,有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混成。冥有與無,以道觀盡,則周盡一體,無不可者。世俗之人,小智自私,闇於大理。或蔽於道之靜,則棄有著空,淪於幽寂,以非無為無;或溺於道之動,則徇末忘本,滯於形器,以非有為有;或使莫為,在物一曲,百家眾技,各矜所長。此道衛所以為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徽宗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拾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疏義曰:真一之原,混淪完具,無象之象,體盡無窮,惟徼與妙,漠然無分。則道本無相,孰為徼妙?自道而降,差數斯睹,昧者執我膠物而物我之見生,此是彼非,而是非之情立,不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根則同也。彼亦因是,是亦因彼,變芒苜而有氣,氣則一也。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歛萬殊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以無為真,以有為妄,拾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無即妙有,有即真無,名相反而實相順爾。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徽宗註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眾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疏義曰:風生木,木生肝,在天為玄,在人為道。道生一,故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一生二,故玄升而入,入而生神。神之為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為天,待是而運,重濁為地,待是而處,坤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咸昌焉。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為眾妙之門也。蓋出則大而赤,入則小而玄,小而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若所謂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玄雖小而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玄之為色,有赤有黑,赤為陽,黑為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凡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為玄者哉?所以為玄,是為玄之又玄,《列子》 所謂色色者也。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者。《易》之為書,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以言入道之序,攝用歸體也。老氏之書,以歸根復命為先,蓋以言行道之頓,以示神從體起用也。《易》託象數老氏同有無以示玄,言雖不同,而相為始終,雖設教不倫,其揆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徽宗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疏義曰:天下無二道,自其同者視之,美惡之名俱泯,一性無性,自本觀之,善惡之端不立。然有上而下為之亞,故有美而惡為之對,有左而右為之亞,故有善而不善為之對。欲有彼而無此,是欲有陰而無陽也,奚可得哉?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神奇為美,以臭腐為惡,而美惡容心,以此為是,以彼為非,而善否相非。殊不知大化無常,瞬息不停,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臭腐神奇,迭運更化。初無美惡,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或是或非,隨得隨失。初無善否,一生一殺,一予一奪,亦相分也,亦相繼也,烏可以差殊觀哉?惟聖人覺此而冥焉,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雖無為而不廢於有為,體真無而常有也,雖事事而一出於無事,即妙用而常無也。夫然故泯好惡於一致,而付是非於兩行。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為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為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雖欲簡之,不可得也,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疏義曰:太易之先,一氣未見,渾淪完具,玄未判離,萬象所以同體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立於兩,有對有待,物物所以為對也。真常散而為群變,一致分而為百慮,同歸別而為'殊塗,未有逃此六對者。是以申於東南則無動而生有,屈於西北則有極而歸無,一有一無,若循環然,有無之相生如此。先難者後必易,多易者終必難,有涉險之難為,天下之難事,則知行地之易,斯無難矣,難易之相形如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非尺之長,無以見寸之短,所謂長短之相形也。山殺瘦,澤增肥,非山之高,無以見澤之下,所謂高下之相傾也。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則聲舉而響應矣,此聲音之相和也。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則形動而影從矣,此前後之相隨也。自其理其事,其形其勢,以至其聲其數,分而為陰陽,列而為四時,散而為萬物,無非六對者。俄造而有,有生於無也;倏化而無,物不終有也。襲諸人間,知有為之匪易;退藏於密,覺無為之非難。登高不可以為長,長非有餘,性長非所斷也;居下不可以為短,短非不是,性短非所續也。高高在上,固非人為,天之自高也;險然處下,亦非或使,地之自下也。以聲律相召,則或官或角,隨鼓而動。其隨序相理,則四時長幼各有其倫。凡涉於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不離於道而於道相去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徽宗註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 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疏義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無為之事,則為出於無為,是乃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蓋用天下,則已接於事矣。惟本於無為,則雖事而未嘗涉為之之邊。舜之不事,詔而萬物成,其得此也。脩道之謂教。不言之教,則以身教而人從之,是乃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蓋設教則既交於物矣,惟出於神道,則雖教未嘗發言之之意。王馳立不教,坐不議,其得此也。且無為則真,有為則偽。從事於務,涉於人為,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上說下教,強聒不舍,未免乎有當有愆矣。聖人朝徹見獨,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於事則無為而成,於教則無言而心悅,舉天下萬物之多,曾不足以芥蒂其胸,次彼六對者,烏能為之累哉?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徽宗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鑒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疏義曰:以一身對羣動之至,以一心膺萬務之求,物或採之,不得六出,事或迫之,不得不動,如監焉應而不藏,如谷焉虛而能受,妍醜美惡,無所辭也。若是,則其於泛應酬醉,蓋有餘裕矣。苟或敵紛趨寂,懼有樂無,則物何自而開?務何自而成?天下何賴焉?是之謂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而生生化化者,不尸其功;自形自色,而形形色色者,不擅其成。有形者以形自奮,有性者以性自適,認而有之則亦惑矣。是之謂生而不有。聖人應世無心而已,其整萬物,非有心於整之也。妻然似秋而綽乎其殺,故殺之而不怨。其澤萬世,非有心於澤之也,煖然似春而與物為恩,故澤及萬世,不為愛人。天無不覆,吾有道以覆其所覆;地無不載,吾有道以載其所載。一根黃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蠛蠓蠔之微,若與之承翼。雖非物刻而雕之,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若刻雕眾形焉,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夫整萬物也,澤及萬世也,覆載天地、刻雕眾形也,未免乎為矣。然而不為戾也,不為仁也,不為巧也,則為出於無為,而不恃其成矣。是之謂為而不恃。四時殊氣,運而無止,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相為消息,相為盈虛,過而不留、天道已行矣。聖人與天為徒,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巍巍乎其有成功。雖無意於立功,而天下歸功焉。方將去功與名,還與眾人,不以為己私分。夫豈認以為實而固有之哉,是之謂功成不居。停燈於釭,前焰非後焰;借明於鑑,今形非昔形。以往者為古,以今者為今,心未及言,所謂今者已遷而為古矣。以有居則有去也,蓋神無尸而無居,尸焉而居人爾。惟聖人執神而固,不傾於物,故在己無居,物莫能遷,不係累於方來,知適來時也,不留情於既往,知適去順也,曾何加損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徽宗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阫。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 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疏義曰:尚者,別而向之之謂。以賢為尚,則愚智相欺,善否相非,民始惑亂,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所謂舉賢則民相軋也。貴者,曰而人之之謂。以貨為貴,則敵羨之心生,不足之慕起,見得忘形,見利忘真,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阫,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惟不以賢為尚,則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民各定其性命之分,孰肯內于外大以為夸,其行不正而為跋哉?各止其所而無所爭斯已矣。莊子所謂削曾史之行,天下之德始玄同者,此也。惟不以貨為貴,則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肯有見於豈而為覬,有見於俞而為覦哉?舉滅其賊心而不為盜斯已矣。莊子所謂撾玉毀珠,小盜不起者,此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徽宗註曰:人之有欲,次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右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坏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疏義曰:眾人見物不見道,故所見無非欲者。聖人見道不見物,故所見無可欲者。所見無可欲者,則以所見勝所睹也,是以靈臺有持而外滑舉消。所見無非欲者,則以所睹勝所見也,是以逐物忘返,失真湛偽。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齅,是人之所欲也。妄庸之人不知五色亂目,五聲亂耳,五味濁口,五臭薰鼻,次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累於厚利者以身徇利,累於名高者以身殉名。若伯夷與盜坏,一則死名,一則死利,几以見浴利之可欲故爾。其熱焦火,得之則喜,其寒凝冰,失之則懼,不能操之而存其心,至於憤亂憤驕而不可係,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豈不惑哉。聖人異乎此,不就利,不違害,知利害之同源;不榮通,不醜窮,以窮通為一致。欲慮不萌,一毫不攖,吾心湛然,物莫能搖,感而遂通,能定能應。止而無所礙,不膠於靜,動而無所逐,不流於動,覆卻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孰能亂之?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得此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徽宗註曰:谷以虛故應,鎰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往天下,一視而同七,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責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春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猒,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日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疏義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古人之貴夫虛也如此。是以遠取諸物,如谷之應,鑑之照,管籥之受;近取諸身,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齅,皆以虛故也。蓋虛者,實之對,實則有礙,虛則無間。外之萬物,內之一身,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以不能無間故爾。聖人不得已而臨往天下,兼愛無私,則一視而同仁,推此加彼,則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無所次擇,付之自爾,無所去取,遣息眾累而冥於無有,夫何容心哉?若舜之聰明文思,堯非不聞也,爻待師錫而後舉之。若鯀之方命圯族,堯非不知也,亦因眾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為心,則舜不得不舉,鯀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包,意其無而非無,則心本虛矣。惟盡心之本,而政虛之極,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豈賢之足尚哉。務內觀者,取足於身,務外游者,求備於物。求備於物則常憂不足,取足於身則敵羨不起。聖人不利貨財,不貴異物者,以取足於身而實其腹故也。實其腹,則收視反聽,精神內守,故贍足平泰而無貴求之念,豈貨之足貴哉。此聖人為腹不為目也。在心為志,則志者心之所之也。形以骨為體,則骨者體之所立也。志強而不弱,則以顯為是。或殉名不息,以富為是。或逐貨無猒,自伐而無功,自矜而不長。其去道也遠矣,故欲弱其志。骨弱而不知強,則行流散徙而中無所守,與物刃靡而外無所勝,胥淪溺而不返,倀倀然莫知所適從,其何能自立乎?故欲強其骨。聖人之用志,卑以自牧,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持後處先,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雄守雌而物莫能勝,知榮守辱而物莫能汙,弱其志者知此。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善建而不拔也。固以執之,萬物莫能傾,善抱而不脫也。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不壞之,相與天地為常,若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強其骨者如此。多知為敗,故使民無知。養心莫善於寡欲、故使民無欲。同乎無知,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德不離矣。同乎無欲,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謂素樸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在天下,民得其性斯已矣。孰使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徽宗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快,能者不敢矜其村,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眾,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成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疏義曰:辮者不敢騁其詞,無所用言也。勇者不敢奮其恢,無所用力也。能者不敢矜其材,以不使能故也。智者不敢施其察,以不用智故也。黜聰明,去機械,省刑罰。凡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眾者,皆禁而止之,雖有知者,孰敢為耶?若舜之時,皋夔稷契之徒,九官咸事而百僚師師,俊乂在服,豈務間間之小,為察察之明,以智為鑿哉?聽倡而行,視儀而動,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為出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疏義曰:治天下者,一於無為而不知有為,則若聚塊積塵,無為而非理。一於有為而不知無為,則若波流火馳,有為而非真。夫惟有為不離於無為,無為不廢於有為,而為出於無為,其於治天下有餘裕矣,豈棄人絕物想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今夫形而上者謂之道,自道而降,莫逃乎物,則萬物之變在形而下矣。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與道無間。總攝萬殊,同於一理,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也。是以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物有生也,因之以政其成,楊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太學生江澂疏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徽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爭#1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有信,所以有用。一根黃之細,若與之扶疏;一蠛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此以往來而不武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為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湛然不撓,浮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為乎?昏昏默默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2,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亨,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強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沖氣是已。沖之為氣,天一為之本,天五為之中,則坤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而不多,不足則予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仲而用之。蓋沖則非盈,有用則非虛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虛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虛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猶如大虛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為量數,豈器之所能囿哉,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徽宗註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疏義曰:莊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蓋淵水反流全一,深靜而平,內明外晦,雖鯢桓之與流止,常淵然自若,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可謂虛也。波之非惡,湛之非美,可謂靜也。道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實;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也;不化而能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文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 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曰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斷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疏義曰:銳如火之銳,不可長保也,故傷。紛如絲之紛,多緒不一也,故雜。挫其銳則不立圭角,渾然而已,孰與動爭?莊子所謂以深為根是已。解其紛,則靈臺有持,外滑舉消,孰能亂之?莊子所謂以約為紀是已。火合并為光,惟和無別,則葆之而不露,韜之而不發,未嘗揚行以悅眾也。莊子於《刻意篇》有曰:光矣而不耀。以言用其光而分夸耀之述,然後為合天德故也。是之謂和其光。麤而非妙,塵所由生,惟同而不異,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未嘗崖異以自處也。莊子於《庚桑楚篇》有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以言衛生之經,在乎與物宛轉,而不在乎離世異俗也。是之謂同其塵。若夫內誠不解,未能忘心,形謀成光,未能用晦,舍者與之避席,又未能自埋於民,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未能若愚,昭昭然若揭曰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利,用之時故說。徙之以銳也,則有時而毀折,能無傷乎?惟有以挫之,則銳斯鈍矣,孰能傷之,然則挫其銳,聖人所以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紛以絲為之,所以分垢汙,合則成體,分則多緒,能勿擾乎?惟有以解之,則雖紛而封,無內外之韆,思慮不萌,機械不作,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合。然則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饒心也,若是則不自矜也,故無秦色,不自伐也,故無驕氣。有異無乖,如《中庸》所謂和而不流。守一處和,如列子所謂大同於物。況應酬醉,無往不當,所謂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徽宗註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疏義曰:心者,神之合,於五行為火。方其有心,猶火之緣物顯照也,及其無心,猶火事已而見灰也。心若死灰,則無心枚爾。草木有生而無知,木至於槁,非特無知又無生也。身若槁木之枝,則遺生忘我故爾。是以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所謂大定持之而循有照也。若然,則非作非止,悟然若亡而存;非有非無,油然不形而神。湛然常寂於其存也,似之而非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滯於一曲而言之哉?湛兮似或存,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徽宗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始見。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應物。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墮於有生,故有象可見。物主然後有象也。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物之尊。故為群物之始。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則道實先之矣。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天在天成象,道生之,帝以妙物,道神之,則舉天下萬物之多,孰先於道者?雖然道無色也,故視之不見;無聲也,故聽之不聞;無形也,故搏之不得。雖有乎出,其出無本無旁,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與莊子所謂不知其誰何同意。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徽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弁。有心於愛人,則其愛不博;有心於利物,則其利不周。蓋以仁為恩,未免於有心故也。且原恩之所起,常本於害,要害之所起,常出於恩。有害而恩隨之,有恩而害繼焉,自然之理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聖人無心於百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故無所不愛,亦無所不利。受施者不報,蒙澤者不謝,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仁烏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已。猶之芻狗焉,其未陳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既陳也,行者錢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用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徽宗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物為一曲#3。 疏義曰:橐之能容,籥之能鳴,二者皆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者也。隨感隨應,果有窮乎?天地之間,一氣潛運,周遍無外,至無以供其求,猶之橐籥也。一物實之,無適非礙,天地之大,豈蔽於一偏,滯於一曲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徽宗註曰:虛己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疏義曰:天地之大,聖人法之,虛其體也,自其用也。攝用歸體,故寂然不動,萬物莫如,以傾其固,以之汎應,有不當乎?從體起用,故動而不窮,既已與人己愈有,以之運量,果有匱乎?虛己以遊世,必迫而後動,故終身言而無失言之愆,無不為而無有為之偽。其於應帝王,蓋有餘裕矣。莊子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徽宗註曰: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疏義曰:凡樂皆出於虛,籥之為器、律度量衡所自出,樂之本在是焉。故《詩》稱以籥不僭者謂此,所謂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者也。聖人得言之,解鳴而當律,有問而應之,無不異此。若孔子之欲無言,孟子以好辮為不得已者,為是故也。彼不能忘言之人,又離曼衍辭至於數萬,書至於五車,是辯者之囿也,雖多亦奚以為?守中者不然,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慎其外而無外較之繁,閉其內而無內韆之繆。目無所見,收其視也,視乎冥冥;耳無所聞,反其聽也,聽乎無聲。復以自知而天地之心坦然可見,守此勿失,雖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奚以譊譊為哉?蓋中通上下有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言之畢不出於此,即多言以交之,不如守中之愈也。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徽宗註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于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疏義曰:盛極則衰,衰極則盛,有形者然也。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有數者然也。既已為物矣,未有逃乎形數者,此所以有生者必有死也。一陰落乎下,一陽徂乎上,未離乎陰陽者,莫不皆然。谷神則異是矣,受而不積,應群動而常虛,陰陽不測,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可以形求、不可以數索,彼形有盡而此無盡,彼數有終而此無終,化出萬有,生生不窮,所謂未嘗死者是已。如彼日月,一往一來,運行不息;如彼維斗,一南一北,斡旋不忒,又焉知其所終哉? 是謂玄牝。 徽宗註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疏義曰: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之所稟者,誰歟?谷神是已。物生成理謂之命,形之所賦者誰歟?玄牝是已。虛而善應,視之不見其形,谷之用無相也。圓而常運,索之莫知其所,神之體無方也。物之所受命者在是矣。赤黑為玄,故《易》稱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陽為牡,陰為牝,故《易》稱坤利牝馬之正,則牝者地之類也。物之所成形者在是矣。谷神玄牝,異名同實,自其常存言之,則謂之谷神,所以況至道之常。自其生出言之,則謂之玄牝,所以明造物之妙。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徽宗註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疏義曰:物之生也,其出無本,故莫見其根。其來無進,故莫見其門。惟聖人視人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則自本自根,而為眾妙之門者。知之如視矣,故直指本宗,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所謂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者,此也。且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處其中,則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物與天地烏可以先後觀哉?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特道之序爾。夫天地所從出者,名之為玄牝,則先天地生者,果可得而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徽宗註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眾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疏義曰:綿綿者,不絕之謂。若存者,不亡之謂。經言湛兮似或存幾是已。至道之極,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僭然若亡而存,可謂自古以固存也。猶火之傳焉,因薪顯照,綠盡復入薪,雖盡而未始有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然而天積氣爾,萬物之所資始,然天之造物,任一氣之自運,非致力以造之也。地積形爾,萬物之所資生,然地之化物,委眾形之自殖,非政力以化之也。大哉乾元,以易而知;至哉坤元,以簡而能。妙用所具,不假施為,自然而已,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徽宗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磚而位乎下。結為山岳,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險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疏義曰:輕清為天,以圓而動,故其體穹窿而位乎上。重濁為地,以方而靜,故其體磅磚而位乎下。天以氣運乎上,則日月也,星辰也,皆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凡戴天者,皆其所覆焉。地以形處乎下,則山岳也,川澤也,皆積形之成乎地者也?凡履地者,皆其所載焉。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無心於萬物。故確然示人以易而其運不息,險然示人以簡而其處不已,此天地所以能長且久也。苟或任機械,恃智巧,簡髮數米物,刻而彫之,是有心於生物也,焉得力而給諸天地之神明?殆將可以數推,可以智測,覆載之功淺且薄矣。若是則有待而生,與物奚擇哉?夫惟不自生,而冥於不生之境,所以能長生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徽宗註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辮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嶮易之利,冬夏不寺#4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其效歟。 疏義曰:天職生覆,故運乎上。地職形載,故處乎下。聖職教化,故位乎天地之中焉。以其用相通,故謂之三才。以其體各立,故謂之三極。以其神不離,故謂之三靈。即是以觀天地之與聖人,進雖異而道則一而已。聖人之治身,不可他求,觀諸天地斯可矣。故此章先言天地而繼之以聖人也。蓋不自生則忘生也,不自有其身則忘身也,忘生而長生,忘身而身存,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自後者人先之,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經所謂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也。川澤納汙,國君含垢,故受天下之垢,經所謂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是也。凡此皆後其身者也,惟後其身,則以柔弱謙下為表,而不與物爭。夫惟不爭,則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身先之道也,是之謂後其身而身先。倀倀而往者,不避川谷險易之利,人所爭也,今則在塗不爭險易之利。違寒就溫者,自然之性,陰陽之和,亦所爭也,今則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悅生而惡死,嚮福而避禍,人之情也,今則外死生,遺禍福。此無他,知身非我有,而四肢百骸將為塵垢,故能大同於物,而不自有其身也。若然,則寓百骸象耳目,而神未嘗有所困,物孰能害之?是之謂外其身而身存。人莫重於一身,聖人治之尚且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知其來不可圉,過之而不守,知其去不可止。不累於形,而體性抱神,與人為徒,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長生久視而與天地並,則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又何難焉?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徽宗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疏義曰:天地者,有形之大也,其異於萬物者,以長久故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其異於眾人者,以常存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所以生生而長久,聖人所以保位而常存,以無私故也。橫私於道,不得道。道者為之公焉,其能無私,以體道故也。韓非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夫不自生也,外其身也,豈自營哉。所以致長久而身存也,是之謂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徽宗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自其未見氣言之則非陰非陽者,道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自其行於萬物者,言之則不離陰陽者,亦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物而言之爾。自道而降,人之可欲,唯善為先,則繼之者善也。夫道一而已,既已謂之善,則分於道矣。其相分也,乃相繼也,故莊子曰:離道以善。蓋善名既立,則渾全既析,而道之體虧。然而九疇以五行為初,五行以水為先,則天一生水,離道未遠也。雖濫而不失其監,淵而虛也。澄之而鬚眉可燭,靜而明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然則上善若水,異乎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矣。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惡,故幾於道。 徽宗註曰: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彙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址;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疏義曰:天一生水,周流無際,其在天也,陽氣勝則融為雨露,敷施以生物,而萬彙以滋。陰氣勝則凝為霜雪,刻制以成物,而萬寶以成。其在地也,疏為江河,聚為沼址;包之反流全一,為泉之深,視之不見水端,為海之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而其養不窮,萬物皆往資焉不匱,而隨取隨給,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其善利萬物,在天為雨露之類,而萬物蒙其澤;在地為淵泉之類,而萬物受其施。然其性解緩,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則於道為近。蓋幾也,幾者動之微,幾動‘而未至特鄉所至爾,故幾訓近。幾於道,則近於道故也。 居善地, 徽宗註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疏義曰:水曰潤下,故由地中行。盈科而後進,故流而不盈也。 心善淵, 徽宗註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疏義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測之而益深也;千里之廣不足以舉其大,窮之而益遠也。 與善仁, 徽宗註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疏義曰:霜露所墜,無有遠邇,極地所載,咸被其澤,可謂兼愛無私,施而無擇矣。 言善信, 徽宗註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疏義日:學海而至于海,所謂避礙而通諸海也。萬折而必歸於東,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政善治, 徽宗註曰: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疏義曰:以出以入就鮮潔,則汙者潔之也。主量叉平,則險者夷之也。若有次行之,以順物之理,無容心也。夫然故澹然無治,而無不治矣。 事善能, 徽宗註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疏義曰:流行順理,故因地而為曲直。隨取隨應,故因器而為方圓。搏之可使過颡,激之可使在山,而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則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也,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徽宗註曰:陽釋之而伴,陰凝之而冰,次諸東方則束流,次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疏義曰:時方在春,陽氣發於上,則冰解而為水,陽釋之而泮也。時方在冬,陰氣極於上,則水結而為冰,陰凝之而冰也。不滯於一隅,不膠於一曲,次諸東方則東流,次諸西方則西流,因物而動,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徽宗註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悍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息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疏義曰:聖人應世,其自為則體道以在己,故治身惟長久之存,所以與天地並。其為人則兼善天下,故利物。處不爭之地,所以其動若水焉。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皡天不宜。蓋君子將有為,又先齋戒以神明其德,則有為不可易也。夫無為則入而與物辨,欲寡過則易;有為則出而與物交,欲無息則難。既以利物為事,是未免有為也,則其於無尤難矣。蓋又宜右上而左乙,宜左屈而右#5,皆所以為尤。惟上善利物,若水之性,上下屈伸,無左右之偏,雖利物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莫能與之爭,萬變常一,物無得以勝之,故無尤矣。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同義。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徽宗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之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疏義曰:物有常量,故盈者斯溢,亦有常勢,故銳者斯挫,則盈叉有虧,萬物之理也。苟不知行巽之權,持後以處先,用謙之柄,執虛以馭滿,消長代謝,與時俱化,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傳》曰:得道者能持盈而不傾。蓋異此矣。以一身對群動,以一心膺萬務,將蟬聰明,竭思慮以應之,則終籍膠錯,曰投其前,雖有至智,或不足以周事情,以物之變無窮而人之智有盡故也。蓋敝精神而妄億度,是為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心勞而日拙,所謂道之華,愚之始也。以智為鑿,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雖得之必失之,可長保乎?《傳》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此之謂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徽宗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息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疏義曰:自券之內無適非真,自券之外無適非偽,金玉富貴皆券外之物,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得與失常相仍,則不可恃而有者也。蓋所寶在我,則無往而不存;所寶在物,則隨得而隨失。寶金玉者累於物,物之去不可止,能無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體恭者,君子之德。驕淫矜夸者,將由惡終。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人所違也,能無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共利之之為悅;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樂道而忘勢。夫豈貴難得之貨,金玉以為寶,以名利為心,富貴之足累乎?故有萬不同皆備於我,至富國財并焉。彼晉楚之富,非此所謂富也。宰制萬物,世莫能先,至貴國爵并焉。彼趙孟之貴,非此所謂貴也。其貴無敵,其富無倫,亙古今而常自若也,是以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徽宗註曰:功成者環,名成者虧,日中則反,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驕盈之患,非知。 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疏義曰:功累之至於高功之成也,然有時而集焉。名修之至於全名之成也,然有時而虧焉。仰觀諸天,日為陽之主,月為陰之宗,日月運行,猶有虧缺,況儻來之功名乎?聖人達萬物之理,知成已俄壞,睹成壞之相因,知盈極叉虛,識盈虛之有數,非得人之得而超然自得,能不累於物而不物於物,謙沖持滿,無復驕盈之息,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視富貴如陰影集身,蚊蟲過前,曾何以為累哉?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今夫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苟知進不知退,進退不已;知存不知亡,保其存而不變;知得不知喪,既得而患失,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蓋有居則有去,功成名遂身退,則功成不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執臣之道者,可不念玆。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1偏爭:疑作『 偏乎』。 #2搏而之不得:疑作『 而搏之不得」。 #3 物為一曲:『 物』 前疑脫『 在』。 #4 冬夏不寺:疑為『 冬夏不爭』 。 #5 左屈而右:『 右』 後疑脫『 伸』。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太學生江澂疏 載營魄章第十 徽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疏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白,陰色也。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矣,故老氏於魄言營。營言有所止也。魂,氣所主也,其字從云。云,陽氣也。出入合散,精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 易》 於魂言遊。遊言無不之也。聖人以神御形,不使神為形所累;以魂制魄,不使魂為魄所拘。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乘之。心有天遊,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周盡一體,異乎狹其所居者。六徹相因,自目徹至於智徹,而充塞無外,異乎六鑿相攘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能外天地,知萬物與我為一而能遺萬物,出入六合,經緯萬方,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拘於形體而滯於魄哉? 抱一能無離乎? 徽宗註曰: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常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道生一,一曰水,故天一生水,於物為精。一生二,二曰火,故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物均有氣,而精神為氣之始;物均有數,而精神得數之先。則精神生於道矣,以昭昭生於冥冥故也。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四時散精而為萬物,則形本生於精矣,以有倫生於無形故也。善抱不脫,守而勿失,則執神而固,與神為一,故精與神合而不離,蓋以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故也。以精集神,而不搖其精,故精全而不虧。以神使形,而抱神以靜,故神用而不竭。以形存神,而神將守形,故形生而不敝。精全而神全,神全而形全,如曰月麗乎天而能久照,如草木麗乎土而能有立,未嘗離也。且人之有生,精為身之本,精具而神從之,則因精集神體像斯具也。精出乎至陰,神出乎至陽,陰精為水,陽神為火。水火本無象也,以鎰燧求焉而水火自至,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可知。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則我身之與天地,其本一也。然則上際下蟠,化育萬物,名為同帝,理亦宜然。奈何倒置之民大愚而終身不靈,重外輕內,志本逐末,役己於物,失性於俗,中心營營,不得須突,寧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菁然疲役,不知其所歸,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不能以精攝魂,魂反從魄,不能以神御形,形反累神,不能自別於物,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不然,載魄以通作則契理,抱一以守靜則合道。無視無聽,惟神是守,而抱神以靜,不虧其神, 慎守汝身,而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由而不變,其大無外;處乎淵泉而不濡,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見其後,孰要其所終?皆一之精通而然也。故莊子曰:聖人責精。舜之戒禹,其曰:惟精惟一。其知此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徽宗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兄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進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政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疏義曰:《易》於《繫辭》言:夫乾,其靜也專。乾之所以專,以靜故也,則專者靜而不維之謂。楊雄於《太玄》言:和柔足以安物。柔之所以安物,以和故也,則柔者和而不暴之謂。且人生大化有四,其在嬰孩欲慮未充,其居也,非有意於止也,故居不知所為。其行也,非有意於動也,故行不知所之。直情任理,無機械之心,而不藏是非美惡焉,故其氣靜而不雜,可以政和而不暴。蓋志為氣之帥,志壹亦足以動氣。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知專氣本於心之一而不變而已。一而不變,則萬物無足以撓心,而氣自專矣。苟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心至于僨驕不可係,是猶強梁者不得蔭死,尚能如嬰兒乎?聖人虛己以遊世,凡橫逆之來,視之如虛舟飄瓦,故能守柔。而心無使氣之強,則與嬰兒奚擇?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問。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氏言政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關尹取其純氣,壺子取其衡氣,言各有當,亦若是而已。古之道衍,無乎不在者,以此。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徽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為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為至,以滌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洗心,孰有一毫之攖?以有言有邇非真,必至於忘言息透,然後為真,以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退藏於密,孰有言為之累?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無所與雜而不虧。其神乘時而為,雖過也,於時不得不過,故過而不悔。循理而動,其當也,於理不得不當,故當而不自得。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徽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愛利之心矣。是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法則固未能息迸,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有為,其於無為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為而不離於無為,而為出於無為,故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初無心於愛民,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初無心於治國,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徽宗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巷舒啟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猒, 能為雌,於是乎在。 疏義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蓋雄以剛勝物,雌守柔而已。知雄而守雌,則不以剛勝物而能守柔也,故為天下谿。蓋谿下地流散所聚故也。聖人兆於變化,動而以天行,則體天道之變化矣。一卷一舒,一啟一閉,與時遷徙,則卷舒啟閉,不違其時矣。知柔知剛,知微知彰,一寓諸庸,則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矣。知持後而處先,未嘗先物而嘗隨物;知守柔而能強,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好之無斁,天下樂推而不猒,能為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徽宗註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疏義曰:真知無知,而不知乃知,故能無知也,而無不知也。苟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聰所以作謀,明所以作哲,聖則事無不通,智則物無不知,聰明聖智,可謂明白四達矣。然而至人洞徹無窮而嘗若昏焉,昭曠無外而嘗用晦焉,可謂守之以愚也,非能無知而何?昔郄雍視盜,文子知不得其死,顏子如愚,仲尼稱亦足以發,然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其得持滿之道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物辮。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疏義曰:神妙物而不測,惟聖人存之,則與神為一。化因形而移易,惟聖人知之,則與化為#1。人存神知化,以與道同體故也。惟與道同體,則與天地合其德,而為萬物之所係,雖天地神明足以配之,萬物雖多足以育之,無不可者。是以其生之也,以遂其性,所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其蓄之也,以極其養,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雖兆於動出,然自生自化,以萬物為芻狗,未嘗有愛人利物之心焉,孰有之哉?故生而不有。雖效於變化,然民日遷善,不知為之者,未嘗有自矜自伐之行焉,孰恃之哉?故為而不恃。雖見於統一,然主治自我而大制不割,未嘗有刻制之巧焉,孰宰之哉?故長而不宰。夫生之者常失於有而有之而能不有,為之者常失於恃其成也而能不恃,長之者常失於宰制雕琢而能不宰,則以微妙眇冥不可測究,出於有物之表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也。非德小而妙,孰與於此?故曰是謂玄德。《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春為蒼天,則玄者,天道之復冬,北辨之時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妙而小焉,天道已行矣,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涎壇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徽宗註曰:有無一政,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鎰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疏義曰:即至神以觀之,意其有而非有,意其無而非無,冥有與無而利用皆所自出入,則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也。即陰陽萬物以觀之,顯而可見,斯謂之有;幽而不測,斯謂之無。別有無於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故三十輻共一轂,涎壇以為器,鑿戶牖以為室,皆顯於有者也,車與器室利在是焉。然車之所以運,器之所以盛,室之所以虛,果何物哉?妙用出於至無,而莫睹其端倪;變化藏於不累,而莫窺其畛域。如鎰無像,因物顯照,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固非有也,亦非無也,應物而不傷斯已矣。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徽宗註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醉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煥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為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睹其述,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疏義曰:有則有礙,無適非實;無則無間,無適非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有之以為利故也。虛故能運量酬醉而不窮,無之以為用故也。目道而降域於兩間,形而上者不離於有,在無亦顯也,故道以器顯,無不廢有;形而下者不外於無,在有亦藏也,故器以道妙,有必歸無。散為五行,水火為用,金木為器,土穀為利,木撓而水潤,火煥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凡在天地之問,孰不資焉?故人賴以為利。降於域中,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有機緘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能自止,孰尸之者?皆天也。故世莫睹其進焉,雖然,無即妙有,有即真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天地之大,秋毫之小,未有逃此者。即車之運,器之盛,室之容以明之,几天下之物所以運,所以盛,所以容可以類知矣。老氏於斯三者,推而明之,舉一以知萬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徽宗註曰: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為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睹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為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疏義曰:離再索得女,外奇內耦,其象為目,則目圍二也。取諸八物為火,火則其光外景,故在性為見。目徹為明,明以作哲,故足以斷天下之疑,五色孰得以亂其明?坎再索得男,外耦內奇,其象為耳,則耳藏一也。取諸八物為水,水則其明內燭,故在性為聞。耳徹為聰,聰以作謀,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五音孰得以汨其聰?睹道之人解乎此,造見見之妙,無形之上,獨以神視,故能見不見之形;造聞聞之妙,無聲之表,獨以氣聽,故能聞無聲之聲。無所不見,無所不聞,視聽不用耳目,而所見所聞無適非真,普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所見不能勝,所睹不知聞,和於無聲,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悅明而淫於色,孰知天下之正色?悅聰而淫於聲,孰知天下之大音?作聰明而聰明日衰,則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其於聾盲奚擇?雖然人者自盲聾爾,豈聲音之能聾盲人哉。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爽。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伴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鎰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疏義曰:人食芻豢,麋鹿食薦,鯽蛆食蛇,鴟鴉嗜鼠,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味?所謂正味,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也。人皆知味之所味者有同嗜,而不知有味味者存,故以芻豢稻粱為足美。然而厚味寔腊毒,雖可以養。體,而失其大體矣。此五味令人。爽也。蓋爽,差也,口爽則失其所謂正味矣。且人之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形不盈仞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則心伴造化也。聖人盡心之真,動而緯萬方,則周流無問,靜而鎰天地,則旁燭無疆,方且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尚何從事於田獵之間為哉?昧者不知,自勝為強,徒以習馳逐為務,或蹶趨以動其心,而不能自得,良心亦從而喪矣,可不謂大哀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徽宗註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次性命之情,而饕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疏義曰:先王懋遷,有無化居,所以阜通貨賄,使交利而俱贍也。蓋利所以養人,而化之則為貨,故交利而俱贍。難得之貨,衣之不可衣,食之不可食,苟以是為貴,則至於次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欲民安性命之情,惟行之為守,難矣。然則聖人不貴異物、賤用物者無他,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是以捐金於巉嵁之山,投珠於五湖之淵,不貴難得之貨,使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孰有行妨者哉?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則以動不為利正大人之行也。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以喻於利非君子之所為也。莊子所以欲擿玉毀珠,而貴夫不利貨財者,以此。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疏義曰:坤厚載物,含萬物而化光,近取諸身則為腹,以厚載而容也。外陽內陰,明兩作為離,近取諸身則為目,以外視而明故也。厚載而容,則未嘗有擇,收而積之,亡處亡塊,故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不能無辨,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有所不及。聖人泯是非,一好惡,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無所次擇,無所去取,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心有眼則開人而賊生也,故聖人不為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息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玆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休迫之恐,欣懽之喜,交溺於心,玆大息所以若身歟? 疏義曰:寵者人之所榮,在下之道也。貴者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居寵而以為榮,則席其寵矣,席其龐則辱。或隨之處貴而以為累,則矜其貴矣,矜其貴則息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累於厚利故也。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累於高名故也。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故也。於是三者操之則慄,所謂既得之,息失之也;捨之則悲,所謂寄去則不樂也。玆寵辱所以若驚歟?集於體者,非有慘怛之疾,為陰陽之寇,則有恬愉之安。涉人道之息溺於心者,非有休迫之恐,以毗於陰,則有欣懽之喜,以偏于陽,一身之息叢起交攻,貴而以為之累,其息亦若此而已。此大息所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徽宗註曰: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古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何辱之有?食夫位也,慕夫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疏義曰:行天莫如龍,合則成體,散則成章,此變化自如,不可制蓄也。能見而不能港,未離乎內覆,可豢之以駕馭服乘,則未免有悔,此可古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也。寵之所以為辱,以是故爾。是以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知在我者有貴於三旌之位也。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知在我者有富於萬鍾之祿也。得持寵之術則居寵而思危,知保福之道則在福而若沖,故能富貴不離其身,而福祿能長且久,何辱之有哉?苟或食夫位而誣偽以取貴,慕夫祿而責汙以取富,知進不知退,昧消長之理,知得不知喪,蔽盈虛之數,則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徽宗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為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 疏義曰:至貴在我,足以并國爵,則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鈴,而求無益於得,以物之儻來寄也。惟時無止,則寄之來不可拒其得之也,於我何加?故至人不以得為悅。惟分無常,則寄之去不可圉,其失之也,於我何損?故至人不以失為憂。昧者不知窮通,如寒暑之序,寄去則不樂,或隕穫於貧賤,受而喜之,或充詘於富貴,得失交戰於胸中,靈臺且為之窒,其不驚者幾希。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豈以得失累其心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息。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疏義曰:以貴自居,未免有息,惟不自有其貴,則可以守貴矣。猶人之一身,認為己有則動輒有礙,知身非我有,則可以保身矣。今夫利勢之重得以據之,賞罰之權得以檀之,威福之柄得以專之,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其貴可謂無敵矣。惟聖人執虛馭滿,不以貴自居,則雖貴而無息。如人之有身,寓百骸以墮肢體,象耳目以黜聰明,離形而不拘於形,去智而不鑿以智,則同於大通,造乎不形,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孰以身為息哉?妄庸之人不能盡性而志勢,累於物以易其性;不能盡心而忘形,累於形以喪其心。以物易性,以形累心,其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徽宗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息?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息,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j 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息。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疏義曰:形骸之內有真君,足以高天下;有真宰,足以制萬物。形骸之外,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苟不知索於形體之內,方且本身而異形,認而有之,皆感也。惟體道者知形形之不形,雖其形化,而吾有不忘者存。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齊壽夭也。顏子曰:回坐忘矣。忘物我也。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無他,知形骸之內有真君真宰者存,故總括百骸者,不能為之患也。古之至人不以利累形,異乎見得而忘形;不以形累心,至於廢心而用形。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得,則吾身非吾有也。見不見之形,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夫孰足以息?心已是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息,豈以世之所榮而為辱,人之所樂而為息哉?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得持寵之術,堯不以位為樂而得守貴之道,幾是已。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猒。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迺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六合內外,無盡無極,則天下大器也。必有出乎器者,然後能運之,出乎器者,道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則天下神器也。必有與於神者,然後能守之,與於神者,道也。聖人體是以在己,故在天下而不淫其性,宥天下而不遷其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下樂推而不猒矣。其次則有明乎物物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知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貴其身而不自賊,愛其身而不自賤,若可寄託而已。夫豈殘生傷性,以身為殉,樊然殽亂為物所役,薾然疲役為物所困,不知保身之道歟?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直以治天下,正謂是也。世俗之君子不知身為生之主,迺殺身以成名,多方以喪生,逐物而不返,危身棄生以徇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所喪多矣,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徽宗註曰: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疏義曰:天三生木,在人為肝,肝開竅於目,故於五事為視,則目主視故也。明兩作離#2,寓象於目,而目之於色,合而後有見,則視以辮物故也。然視而可見,未離乎色,或高或下,可得而辯也。妙道非色,青然空然,曾無兆朕,視之不足見也。其平坦然,孰辯高下?列子所謂太易未見,氣是已。渾淪之初,氣且未見,其平可知,故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徽宗註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穊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疏義曰:天一生水,在藏為腎,腎開竅於耳,故於五事為聽,則耳主聽也。水荐至為坎,寓象於耳,而耳之於聲,辮而後能聽,則聽以察物故也。然聽而可聞,未離乎聲,迭為清濁,莫之能間。妙道無聲,寂兮寥兮,曾無音響,聽之不足聞也。風濟籟息,概而有間,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其穊可知,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徽宗註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疏義曰:氣變而後有形,有形而後可得。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未始有物,循之而不得也,是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者矣。有形斯可搏,道之無形,孰得而搏之?經所謂大象無形,則象之大者,孰有過於道者哉?夫惟無形,故其大無外也。 此三者不可致詁,故混而為一。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辮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疏義曰:太易未判,列子所謂色色者未嘗呈是也。色色者無色,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列子所謂聲聲者未嘗發是也。聲聲者無聲,孰辮清濁?大象無形,列子所謂形形者未嘗顯是也。形形者無形,孰為巨細?雖使離朱當晝拭訾望之而不見其形,則目無所用其明也。雖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則耳無所施其聰也。雖使知與喫詬之徒索之而終莫得,則形無所竭其力也。自其視之不見,言之則曰夷。自其聽之不聞,言之則曰希。自其搏之不得,言之則曰微。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列子所謂渾淪是也。謂之渾淪,則以氣形質具混為一,而未相離故也。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無,玆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辮而有數,玆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疏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神實妙焉,則神固形而上矣。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神則陰陽不測也。速不疾而行不至,惛然若亡而存,是之謂其上不皦。形而下者謂. 之器,而道實寓焉,則道亦形而下矣。不偏于陽,非獨陽而生,不毗于陰,非獨陰而成,道則一陰一陽也。可以約,可以散,在無亦顯,是之謂其下不昧。蓋皦與皦如之皦同,皦言明也,不皦則幽而難知矣。昧與昧谷之昧同,昧言幽也,不昧則辮而有數矣。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徽宗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疏義曰:繩以約物,使不失其直,繩繩則不出乎防範檢押之內也。道之倫經,有條而不紊,若晝夜之有經,一晦一明無或渝也,故謂之繩繩。然深妙眇冥,無有無名,莫測其幽明之故,是以不可名。若然則復本歸根,一毫不留,非特未始有物,而又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者矣,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是之謂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徽宗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諸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疏義曰:有狀故可見,道無見也,亦不離見,故為無狀之狀。有形故可象,道無形也,亦不離形,故為無物之象。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意其有而非有,恍兮惚而中有物也,意其無而非無,惚兮恍而中有象也,如太虛一虛化出萬有而未始有封,含蓄萬象不睹其端倪也。如一性無性,應物不窮而深不可測,靈智自若而莫究其妙用也。即有而無,有實非有,即無而有,無實非無。若日月去人遠矣,以方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不旋頃而水火自至。水火之為物,不可以有無期之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故謂之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徽宗註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疏義曰:道之全體,混成完具,贍之在前,孰原其所始?忽焉在後,孰要其所終?莊子所謂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是也。迎之隨之,曾何有見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彊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桔槁。為我者廢七,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詁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道雖非陰陽,亦不離陰陽故也。昧於道者分陰分陽,或悅生而累形,則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彊陽;或趨寂以忘身,則溺於道之靜而止乎桔槁。為墨氏之兼愛者,為人而廢義,至於無見於畸。為楊氏之為我者,為我而廢仁,至於蕩而不法不該不偏,蔽於一曲。豈古之道哉?古之道有不廢無,不可致詁而非有,無不外有,是謂恍惚而非無。操此為驗,稽此為次,以應萬變,以對方來,變通足以盡利,鼓舞足以盡神,其於御世,無不可者,此古之道也。是道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維綱宰制,凡囿於物,未有外是而能立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惟能探物之先而知其始,則道之倫經皆在我矣,故曰是謂道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竟 #1則與化為:『 為』 後疑脫『 一』。 #2明兩作離:『 離』前疑脫『 為』 。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太學生江澂疏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徽宗註曰: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疏義曰:有上古,有中古,古之士則上古之士也。有上士,有下士,善為士則上士之類也。則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與不善為士異矣。善為士者,其才上達,志於道而與乎神,明於天而通於聖,淵乎其不可測,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蓋視之不見名曰微,道無形也,不可以目視,惟知微,故與道為一。《書》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常無欲以觀其妙,神無是也,不可以有求,惟入妙,故與神同體。《易》所謂神妙萬物而為言是也。玄之為色,有赤有炁,以能陰能陽故也,而、天之色在是焉。《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者,以此。能玄能黃,則與天為徒矣。通之為義,往來不窮,以無物能礙故也,而聖之事在是焉。《傳》所謂事無本通之謂聖者,以此。同於大通,則入自聖門矣。古之善為士者,自微妙以至玄通,奭然四解,淪於不測,非若水之深可測,穴之深可究。杜德機而不示,豐智源而音出,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腫。若火事已而見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世何足以識之?昔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得此故也。盍圃澤多賢,里非無仁也,歷年四十,處非不久也,而人無識之者,則以圖滑疑之耀,去形謀之光,人無得而識之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謂是。故爾。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則以盛德若不足,猶之良賈可也。此顏子如愚,孔子賢之。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徽宗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疏義曰:天統元氣,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故其高不可俄而度。地統元形,非止山林川澤之謂也,故其厚不可俄而測。穹窿乎上人,謂其圓以覆。磅磚乎下人,謂其方以載。特擬諸容而強名之爾。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亦天地已。如下文所云,皆強為之容而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徽宗註曰:豫者,圖息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疏義曰:先事而圖謂之豫,則豫者圖息於未然。後事而圖謂之猶,則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外游為至,以忘物為善,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敢肆也。故於事之未至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先事而圖,如冬涉川。於事之已成者,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後事而圖,若畏四鄰。蓋川者難之所在,冬而涉之,人所病也,若冬涉川,豈得已哉?鄰者比而恤己,使之相保,人所善也,若畏四鄰,豈失己哉?然則有而為其可易耶?《易》言:君子將有為,將有行,必先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謂此也。 儼若容, 徽宗註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猒, 故其狀義而不朋。 疏義曰:入而與物辨,則墮肢體,寓百骸,而其形為可踐;出而與物交,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而容止為可觀。儼若容,則出而交物,容止可觀之時也。《語》所謂望之儼然,《記》所謂儼□ 若思,皆此意也。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全德之人貌允空虛,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況見於動容貌之際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遠之則有望,在彼為無惡,近之則不猒,在此為無斁,則其使人之意也消,固不難矣。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曷嘗脇肩諂笑,以自招其辱哉? 渙若冰將釋, 徽宗註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涣,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輆,所以為涣。 疏義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陰凝之而為冰,猶神之化形也。陽釋之而為水,猶形之化神也。水之與冰,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知守形而不知盡神,故如水之凝,生於水而遏水。通於大同者,知忘形而能與於神,故如冰之釋,汎然而無留礙也。《易》於風行水上為泱,而《說卦》以謂涣離也,則泱之為義,以離物遺人而無繫較故也。惟離物遺人,則若冰解凍釋矣,孰有繫較者乎?與夫其寒凝冰者,固有間矣。《太元》曰無所繫較者,聖也。涣若冰將釋,所以通有以入聖歟? 敦兮其若樸, 徽宗註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疏義曰:《易》所謂敦仁言於仁為至厚,《記》所謂教化言於化為至厚,則敦者厚之至也。惟民生厚則性本厚矣,因物有遷則厚者薄矣。惟善為士者,復性之本,不與物遷,則如木之樸,樸而圍之,有象可見,未形為器,其厚可謂至矣。與夫以斤斲之,析其渾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蓋有間矣。 曠兮其若谷, 徽宗註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疏義曰:《詩》所謂曠野,言其地之至廣,《傳》所謂曠日,言其時之至廣,則曠者廣之極也。方寸與太虛齊空,則心原無際矣。無所不包,實無所包,則其室常虛矣。惟善為士者,政虛之極,盡心之真,如谷之能受,受而不積,如谷之能應,應而不著,其廣可謂至也。與夫六鑿相攘,自狹其居,以實妨道,動輒有礙,蓋有間矣。 渾兮其若濁。 徽宗註曰:不劌彫以為康,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汙者異矣。 疏義曰:至人之遊世,和光而同塵,毀方而丸合,大廉不嗛,行非刻制,未嘗劌彫以為康也。不多辟異,為在從眾,未常矯激以為異也。行險而順,與物宛轉,不立圭角,渾然而已。眾人昭昭,我獨若昏,似濁而非濁也,與修身以明汙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徽宗註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休迫之情、遑遽之勞,故曰徐清。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疏義曰:自豫兮若冬涉川,至渾兮其若濁,應世之述如此,則以體道故也。惟體道,故動靜不失其時,而物莫能累,是以守靜為筒。效物以動,則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非流於動也,故動而無所逐,物孰能濁?有所定矣。感而遂通,則定而能應,至無以供其求,非膠於靜也,故止而無所礙,物孰能安?夫物之不能濁,以靜之徐清故也。物之不能安,以動之徐生故也。靜之徐清,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也。雖濫而不失其濫,汨之而常自若焉,萬物豈足以撓其心?動之徐生,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不滯於一隅,時出而應之焉,萬物豈足以係其慮?蓋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與《易》言來徐徐同義。一動一靜,因其固然,不悖於理,付之自爾,不拂其性,皆安行而自適,又孰有休迫之恐、遑遽之勞哉?安有止之意,作之而不止甚矣,止之而不作亦甚矣。時作時止,不為物所係,孰能傷之?蓋為物所係則止矣,惡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疏義曰:以囷藏禾,禾盡囷虛,以皿藏水,水盡皿虛。草之盛物,取之如禪;贊之盛物,有時而匱。以有積,故不足也。至無以供萬物之求,至虛以應天下之實,以無藏,故有餘也。道運而無積,用之或不盈,至人保此道而無積,亦虛而已。苟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是猶擅一壑以自足,亦以小矣。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豈有滿假之累哉?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徽宗註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常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末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曰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疏義曰:有形則有新敝,有數則有成壞。春先夏從,更旺更廢,運為四時,新故相代者然也。言唱手執,迭盛迭衰,散為萬事,成壞相因者然也。此皆墮於形數之域,故方新而敝,成已俄壞,莫能進之者。惟道無體,不囿於形,故能新能敝而未嘗敝,不麗於數,故能成能壞而未嘗壞,以虛而不盈故也。今夫木之為物,蕃鮮於春,而搖落於冬,則始榮而終悴也。火之為物,用之彌明,而撲之則滅,則初明而末熄也。出一而旦,入六而冥,曰雖為陽之精,未免乎中則昃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月雖為陰之精,未免乎滿則虧也。凡以域乎形數,故有新而弊,隨之有成,而壞繼之故爾。有道者虛而不盈,超然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弊能新,能成能壞,而未嘗敝,未嘗壞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徽宗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眾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政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疏義曰:同乃虛,虛乃大,大則能兼覆而不遺,故列子言莫貴乎虛。虛則靜,靜則明,明則能照臨而無外,故列子言莫貴乎靜。無所於忤,是之謂虛,而天下之實莫逃乎虛。一而不變,是之謂靜,而天下之動不離乎靜。此莊子所以言虛靜者,萬物之本也。經所謂淵兮似萬物之宗,亦若是而已。夫萬物以形相礙,以數相攝,囿於形則為形累,攝於數則為數役,必有超形離數者,其惟虛靜乎?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以不礙於形,不攝於數故也。然而探虛靜之本,雖得之自然;要虛靜之至,必在乎政守。致之至於極,守之至於篤,則靜也,虛也,得其居矣。極猶屋之有極,群村必集,是眾會而有所至也。篤猶馬之盡力,千里可至,是力行而有所至也。致虛期於極,則滌除外慕,一疵不睹,非特未始有物,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焉,此致虛而要其極也。守靜者期於篤,則湛然常寂,未始其攖,非特離動而靜,至於即動而靜焉,此守靜而至于篤也。致虛極而不以實妨之,守靜篤而不以動違之,則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吾心常寂。夫芸芸之物,情偽不同,是謂萬態。擾擾之緒,迭作不常,是謂萬變。萬態雖雜,心常徹者,虛足以受之也。徹與心徹為智之徹同。萬變雖殊,而心常寂者,靜足以應之也。寂與寂然不動之寂同。致虛守靜,一至於此,是為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其為天樂,孰大於是?觀莊周之論虛靜,既曰一心定而王天下,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蓋能定然後能應,所謂常徹常寂,一心定之謂也。惟夫一心定,然後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其為樂可勝計耶?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徽宗註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疏義曰:氣變有形,形變有生,在形而下無動而不變也。故萬物之變,在道之末。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所以能寓乎萬物之上焉。且萬物之生,役於造化,隨序相理,橋運相使,出於機而流形,則生有所乎萌,入於機而復命,則終有所乎歸。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方其並作也,由乎艮之徑路,達乎震之大塗,茁而出,萌而明,職職陳露,趨于動出之塗。聖人達萬物之理,虛靜之中,徐以泛觀,知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雖動而不離於靜,雖出而未嘗不復。觀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焉。在《易》之《復》有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復者,小而辨於物之時。辨於物,則至靜而未始其攖,萬物無足以饒之者也。聖人無常心,一本諸天地,雖紛而封,雖櫻而寧,交物而不與物俱化,非離交而辨能,即交而辨焉。故於物之並作,以觀其復也。雖然老氏於觀復則曰並作者,蓋有無作止。理雖異,致其於達觀則一而已。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徽宗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疏義曰:物生若芸,徐動而出,則芸芸者,動出之象也。然物之動出,各因其時。觀四時之運行,具八卦之妙用,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入,與之入而不連。故自春租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祖冬,為人入而之天。自其出而之人言之,則出乎震,而震者束方之卦也,於時為春,物皆萌動;相見乎離,而離者南方之卦也,於時為夏,物皆蕃鮮,所謂芸芸並作,英華發外也。自其入而之天言之,則說乎兌,而兌者西方之卦也,於時為秋,物皆至於揫斂;勞乎坎,而坎者北方之卦也,於時為冬,物自歸根,所謂去華就實,歸其性宅也。芸芸並作,則春氣發而百草生也。至於英華發外,則苗而秀矣。去華就實,則正得秋而萬寶成也。至於歸其性宅,則復於無物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播大鈞而凝形者,性命固已均稟。莊子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則散專精而孕氣者,精神固已和會。然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能順其命,乃能正其性,是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人之有生,精具而神從之,能保其精,乃能合其神,是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惟知性達命,然後能自本自根,全之而不傷性;因精集神,然後能得母知子,守之而不失。所謂精全則神王,非因精集神者能之乎?所謂盡性至於命,非知性達命者能之乎?莊子論純素之道,始言一之精通,終言不虧其神,則精全神王可知也。孟子論盡心之道,始言養性事天,終言修身立命,則盡性至命可知也。能明乎此,其於達萬物之理,特觀復者之餘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徽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亙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疏義曰:域留動之形者,貌象聲色至真咸寓,孰不稟自然之成理?莊子以謂物生成理謂之形,經言物形之是已。變保神之性者,秀鍾靈備,誘然皆上,孰不具固有之儀則?莊子以謂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詩》言有物有則是已。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形,未形之初,雖有分也,且然而已,未始有間,所謂且然無問謂之命也。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變而不窮,非終始之可期,非時數之所拘,亘古今而常存也。性與生俱,生不為貴賤加損,不為死生存亡,更萬形而不易也。惟全其形生之人,存其形而不弊,抱其生焉而不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歸於寂定,物不能遷矣。去智與故,若所謂不識不知、不恃智巧是也。歸於寂定,若所謂寂然不動、大定持之是也。惟能如此,故知命之在我而不與物化,如彼春夏,復為秋冬,動者靜,作者息,而知所止矣。蓋春言天造始物,秋言人為之成,夏言人事之戒,冬言天道之復。自春祖夏,為天出而之人;自秋祖冬,為人入而之天。春夏先,秋冬後,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則芸然流形者,各復其根而不知矣。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蓋亦如此。若然則體性抱神,中以自考,而復命之常,惡往而不暇?莊子曰:無為復樸,體性抱神。蓋無為復樸,則純素是守,故能體性抱神。《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蓋因性而厚,則外無所待,故能中以自考。夫惟如此,則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其於復命也何有?經於有物混成章言: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終之以逝曰遠,遠曰反。亦以歸於寂定,然後可以復命之常故也。是以先曰歸根,後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徽宗註曰: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疏義曰:即經緯以觀常與變之理,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而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常之與變,猶經之與緯,則常者對變之辭也。然成而不變,物所謂常。變化無窮,道所謂常。物所謂常,以常故弊。道所謂常,以變故常。惟復命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波之非惡,湛之非美,雖歷萬變於不可為量數之中,曾無以易其真常信,所謂萬變不能遷也。若然則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是謂無間。不以頃久推移,未嘗止也,是謂無歇。無間無歇,與道為一,則亙古亙今,獨立不改,如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相為長久,如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相為無窮。其為常也,無以易此。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疏義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道之常不與物遷者,以靜而已。惟靜也,故不與動俱馳。於萬物並作也,以觀其復;於物之芸芸也,知歸其根。觀復而歸根,則其靜也,萬物莫足以傾之矣。是以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蓋徹者,不為物所壅之謂。目不為色所壅,故見曉而為明;耳不為聲所壅,故聽瑩而為聰;鼻之於臭,徹而為顫;口之於味,徹而為甘;以至心不弊於思慮,徹而為知;知不昧於物理,徹而為德,是所謂六徹相因者。自目至於知,六者相因不壅,以虛一而靜故也。虛則靜,靜則明,明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天地雖大,於此乎可觀;萬物雖多,於此乎可形。靜乎,天地之鎰也,萬物之照也,非知常者未易臻此。 不知常,妄作,凶。 徽宗註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玆妄也已。 疏義曰:心與道合,則作無非真;心與道離,則動無非妄。聖人者,道之極也,所以知道之常而不與物遷。故作則契理,無適而非真,每與吉會,無往而不動,動必迪吉,履必考祥,作德心逸曰休,作善而降之百祥也。不知常者,作無非妄,去道愈遠,與接為構,隨物轉徙,曰以心鬬,觸塗生患,故妄見美惡。牽於好惡之私,而不知齊美惡於一理,故與道違,妄生是非。惑於毀譽之偽,而不知化是非於兩忘,故與道異。蓋道不可須臾離,既與道違,又與道異,則馳其形性,寇於陰陽,且不足以固其命,禍莫大焉,故凶。《易》於《序卦言》:復則不妄。蓋復小而辨於物,是為無妄。無妄者,天之命,萬物之所聽也。故其《象》言: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無妄則物得其性矣。至於迷而不復,則失性而窮,不能生生,玆妄也已。 知常容, 徽宗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疏義曰:道之真常,一而已矣。體道之一,以觀天下,則紛錯萬殊,同為至妙,孰有是非美惡之辨哉?蓋排非提是,則生於有執;好美惡惡,則索于自徇。至人去有執之累而忘是非,冥自徇之私而齊美惡,玆無他,知常而已。知常則虛己遊世,達乎無疵,是非美惡不藏於心,然後能廣乎無不容矣。聖人之治虛其心者,以此。 容乃公, 徽宗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疏義曰:因物有見,則私於自徇。冥道無心,則公於大同。聖人家天下而兼覆,子兆民而均育,無容心焉,故不獨親其親而愛無不至,不獨子其子而慈無不廣,又何私之有?即天地觀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凡囿乎兩間,未始逃於覆載。容乃公者,蓋亦如之,故觀天地則見聖人。 公乃王, 徽宗註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猒。 疏義曰:道者為之公,人之所共由,此《記禮》者載仲尼之言,所以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治之要在知道,而聖道為群心之用。聖人以道出治天下,以心受道,是以親而慕之,懷而歸之,發於心悅誠服,至於悠久不息,天下樂推而不戢矣。《易》所謂百姓與能,此之謂也。 王乃天,天乃道。 徽宗註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疏義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域中四大,王處一焉。此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者未離於有數,而為數之宗;大者未離有體,而為體之極。輕清在上,兼覆廣容,此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得之而職氣覆,地得之而職形載,聖得之而職教化,此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王者,人道之極。能盡人道,則與天通,豈非盡人則同乎天歟?莊子曰:王者天道。則王乃天可知也。天者,道之大原。能以天為宗,則與道為一,豈非體天則同乎道歟?經曰:天法道。則天乃道可知也。《詩》之《大雅》於無聲無臭而曰儀刑文王,蓋文王所為,實與天合,欲自天之道,則亦儀刑文王而已。是盡人則同乎天也。又於不識不知而曰順帝之則,蓋妙道之行,實同乎天,欲探道之妙,則亦順帝之則而已。是體天則同乎道也。周家之盛,聖作明迷,相守一道,歌於聲詩,所以為三代之顯,王者每得乎此。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徽宗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疏義曰: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者,道之久也,故萬世無弊。所謂會古以固存者,是以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故庶物得之者昌。聖人體道而為道之極,參萬歲而一成純,故關百聖而不窮。亙古今而無弊,故蔽天地而不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孰能危之?可謂沒身不殆矣。殆以怠,故近凶,所謂怠勝欽者堤已。幾以戒,故近吉,所謂吉之先見是已。不殆則動皆契理,每與吉會,無妄作之凶。自非聰明睿智,足以知道之常者,疇克爾。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啖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悔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在之則存而不亡,所以防其淫;宥之則放而不縱,所以守其遷。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天下將自化,與一世而得澹泊焉。聖人以道往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則人雖有知,無所用之,孰有欣欣之樂,瘁瘁之苦哉?無欣欣之樂,則其心恬惔而親譽不及;無瘁瘁之苦,則其心夷懌而畏侮不至。無欲而自足,無事而生定,舒通平泰,自得其得,莫之為而常自然,則以相忘於道故也。所謂下知有之者,以此。孟子謂王者之民皡皡如也,惟此時為然。 其次,親之譽之。 徽宗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疏義曰:所以利物者莫如澤,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周則發政施仁,所謂澤加于民也。所以致治者莫如法,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至周則庶事皆備,所謂法傳于世也。澤加于民,法傳于世,以此撫育,則若保赤子,天下愛之如父母,孰不懷慕而親.之乎?以此施設,則厥聞四馳,貴名起之如日月,孰不樂推而譽之乎?帝之所興,王之所成,其德業發越於天下,有不可得而掩者,未有不本諸此,所謂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也。若然則大同之道虧,與所謂下知有之,蓋有問矣。蓋大同則民無知無欲,何親譽之有?昔舜有羶行,百姓慕之而鄧墟來十萬之家;文王有靈德,民皆樂之而靈臺歌始附之眾。帝王之治所以致民之親譽者,以此。然則聖人豈有心於民之親譽哉?盛德大業加施乎天下,而親譽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其次,畏之侮之。 徽宗註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而刑政賞罰所以輔道而行也。以刑政明天下之防範,使民有所守,以賞罰示天下之好惡,使民知所禁,一本於道而已。若乃一於政刑而不出於道,適足革其面,未足以革其心,故畏之而已,又至於侮之焉。蓋道之以德,則政已行矣。道之以政,則非有德也。齊之以禮,則刑以舉矣。齊之以刑,則非有禮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以畏之者,以民有逐心故也。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又有如楚子之與陽虎,或侮之者焉,以不知以道在天下故也。若夫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而法度明,不賞而勸,不罰而畏,而勸沮公則有道存焉,此又非有欠而為之次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徽宗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疑,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洪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疏義曰:經曰:其中有信。則信之有諸已得之於自然。莊子所謂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則以至信得之於自然也。《記》曰:大信不約。則信之孚於人,無待於或使。《記》所謂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則以信不足,失之於或使也。蓋至信則因其固有,未始有疑。信不足則失其至真,故有不信。太上,下知有之,則民性素樸,同乎無知,所以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民俗凋弊,澆淳散樸,所以機巧之變生,而有不信者焉。《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蓋至精默契,適當人心,是謂至信。若乃為機變之巧,使俗惑於辨,而無所用耻,又何信之有?以信不足故也。 猶兮其貴言。 徽宗註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疏義曰: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以道觀言,則言者未嘗有言,而有真君者湛然而獨存矣,故天下之君正也。且言者風波,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言豈可易,則所謂猶兮也。言弗敢輕,所謂貴言也。古人所以戒金人之銘,慎白圭之玷,則知言之不可易而弗敢輕,亦以明矣。是以聖人言而民莫不信,故言而世為天下道。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故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夫何故?以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故四方罔不是孚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徽宗註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疏義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特其緒餘土直以每成功爾,是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惟其功成事遂,則措天,下於安平泰,民無所施其智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已。食以止分,故甘;服以法華,故美;俗以不擾,故安;業以存生,故樂。是皆聖人之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而然也。故百姓曰用而不知,則謂我自然,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昔堯治天下,康衢有莫匪爾極之謠,所謂太上之治,其在玆時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太學生江溦疏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徽宗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迺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君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疏義曰:道之大全,冥於渾淪之中,德分於道,判為剛柔之用。蓋道不可致,故道失而德。德不可至,故德失而仁。仁可為也,為之則近乎義,故仁失而義,所以去道為愈遠。即其本而論之,則道一而已,楊子所謂合則渾、離則散者,此也。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臆見曲說,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老君小弁義為所見者小,殊不知七義不外道德,道德不廢,安取七義?探本言之,雖曰攘棄仁義,而仁義已行於道德之問矣。是其心豈真以仁義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其小仁義,乃所以尊仁義也,正莊周所謂蔽蒙之民也。後世之士蔽於俗學,無高明之見,聞老氏之道術,遂至於狂而不信,而卑汙蹇淺。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愈有以發之也。 智慧出,有大偽, 徽宗註曰: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疏義曰:至德之世,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適性而足,安分而止,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何所用其智力哉?迨其欲慮一萌,物誘於外,智不足則困,力不足則怠,失其常然,而汨於人為,所謂民智力竭而以偽繼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欲斯民之復其性,亦不以智治國而已。故列子曰: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徽宗註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談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義曰: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名必從之,然名常生於不足。夫君子之成名,莫大乎忠孝,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斯為孝。苟以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謏其親,非所謂孝。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斯為忠。苟以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諂其君,非所謂忠。惟不謏其親,不諂其君,則忠孝之心無餘蘊矣,此臣子之盛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徽宗註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鷙卓驚之行。驚愚而明汙,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疏義曰:無受之初,性與道冥。有受之後,性與道違。惟與道冥,故無.差殊,所謂道與之性,一而不雜者是也。惟與道違,故有分際,所謂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者此也。原性之始,妙本渾全,聖智下愚,初無殊品。離道者外立其德,失真沈偽,迷而不復,因愚顯智,遂有聖名。聖智立,則不能因性之自然,而天下始有喬詁卓鷙之行。喬則為亢,詁則窮深,卓則難及,驚則不群,皆非平易中正之行也。於是飾智驚愚,脩身明汙,譽堯而非桀,曾不知兩忘而化其道,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正與莊周言悅聖耶是相於蓻,悅智耶是相於疵之意同矣。惟知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因性自然,舉天下於無為之治。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蓋民復素樸,安其性命,則與一世而得澹漠,其利可勝計耶?信所謂其利博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徽宗註曰:孝慈,天性也。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疏義曰:百行以孝為本,三寶以慈為先。孝慈之心生於固有之天性,非偽為也,非外鑠也。至於蹩躠為仁而行非自然,踶跂為義而強於用力,則是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民將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是謂反其性而復其初也。若然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獨子其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端正而不知以為義,其於孝慈也,人皆有之,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徽宗註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寄之類也。 疏義曰:不羞惡則無以知恥,不知恥則無以行義。人之為人,以行己有恥為貴,以見利思義為先,能明乎此,然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歸於君子之途矣。彼其為機變之巧者,則純白不備,道所不載,是無所用恥也。彼其有歌利之心者,則依仁蹈利,讎偽假真,是不顧其義也。無所用恥,不顧其義,則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蓋異於非其有而取之者幾希。所謂是皆穿寄之類也者,以此。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徽宗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曰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松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七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據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疏義曰:夫寒積而成暑,非一曰也。觀天時以驗人事,則先王以人道治天下,由簡以至備,所以至周而彌文。當是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郁郁之文莫盛乎此。然文極則弊,息於滅質。文有餘於尚華,質不足於居實,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凋於浮偽,曰淪於私欲之習而蔽於小智,可不因其弊而救之乎。老氏當周之末,方將松其弊而使之反本,意有在於斯也。故攘棄七義而復性於自然,絕滅禮學而相忘於道術,雖聖智亦在所擯而莫之尚。蓋欲天下輕末而重本,松其述故也。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或因或革,或損或益,先王之道若循環也。然文之弊不可不救之以質,亦猶四時之序,夏反而為秋也。據文莫若質,故令有所屬也。下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有所屬也。 見素, 徽宗註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疏義曰:繪事以素為先,故《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則白,立而釆色,未彰素者,性之質也。謂之素,以其不染諸物而已。見素則明白洞達而一疵不睹,純白內備而機心不存,所謂純粹而不雜者也。與莊子言明白入素,與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同意。 抱樸, 徽宗註曰: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器用以樸為本,故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則體全而雕琢不加。樸者,性之真也。謂之樸以不雕,以人偽而已。抱樸則敦兮若樸而性真自全,無為復樸而虛靜恬淡,所謂靜一而不變者也,與莊子言純樸不殘之樸同意。然則素樸者,民之常性也。復性之常,則淡然無欲,自得其得,正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也。 少私寡欲。 徽宗註曰: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疏義曰:蔽於一己則失其大同,故自營為私。牽於利欲則汨其虛靜,故養心莫善於寡欲。私也欲也,皆外游是務而非內觀,皆人偽是滋而非性真。惟少私寡欲,然後能定乎內外之分而知所輕重,辨乎真偽之歸而明於本末,不遷其德而德全,不淫其性而性復,為無為,事無事,而聖智之名泯矣,有治天下者哉。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疏義曰:理猶里也,可以數度,惟務學乃能探其頤。道猶路也,人所共由,惟絕學乃能極其至。學以窮理,學之始也,故經曰:為學日益。蓋方其務學以窮理,則思慮善否而求諸心,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是未能忘於思為之益也,能勿憂乎?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者,此也。學以致道,學之終也,故經曰:為道日損。及其見道而絕學,則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亡,損之又損而未始有物。夫未始有物,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任其性命之情,樂以忘憂,無適而不樂焉,故無憂。孔子以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者,此也。文子曰: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而終之以可謂能體道矣。然則為道日損故能樂道於此,明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徽宗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善,惟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疏義曰:以道冥物,則同異所以藏。以物分道,則同異所以立。自情言之,以唯為恭,以阿為慢,善在所好,惡在所惡,固不同也。即理觀之,唯阿之發同於一聲,善惡之混根於一性,孰為差別?小智自私,任情者也。任情而私,則各植一見,妄為區別,所謂離而為二者此也。達人大觀,任理者也。任理以觀,則總攝萬殊,同為至妙,所謂本實非異者此也。聖人冥心於道,不見一物,然於世人善惡不能有廢者,蓋不欲自異於世而已。是以出而經世,在宗廟朝廷,則便便以辨治為事;與下大夫言,則有侃侃之和;與上大夫言,則有誾誾之欽。所以稱情而為禮,為禮以辨異,故其不齊如此。若然則惡者遏之,善者揚之,以公天下之是非,以示天下之好惡,惟恐不至,則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俯而與人同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徽宗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息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息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疏義曰:偶而應之者,道也。道則何思何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寂然不動也。匿而為之者,事也。事則有思有為,吉凶與民同息,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體道者入而伴於天,故無憂;涉事者出而交於人,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息者鮮矣。惟翼翼以盡其欽,業業以致其慎,然後能動必迪吉,而無悔吝之虞也。《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是皆戒之至也。蓋恐懼脩省,思息豫防之,若伯益之做戒無虞是也。畏天之威,以保天下,若高宗之嚴恭寅畏者是也。觀此則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厥理明矣。 荒兮其未央哉。 徽宗註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為一。 疏義曰:六合之大,萬物之多,擾擾萬緒,日投其前,紛籍交錯,繁不勝應,則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也。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叢至杳來,無有端倪,則難終難測而未始有極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謂善惡特未定也。世人善在所可,惡在所否,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雖有可否,皆出於彼是之域而已,烏知所謂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者乎?惟達者釋智,回光照之于天,則物之所謂彼者,果有定體耶?無定體,則物無非彼矣。物之所謂是者,果有定體耶?無定體,則物無非是矣。物無彼是,則知通為一,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又何議議然區別於其間哉?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徽宗註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眾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睹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也。物之孕氣,以陽而熙,陽融而亨故也,以陰而凝,陰止而靜故也。或熙或凝,唯其時物,則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眾人失性之靜,與物俱化,務外游不務內觀。如悅厚味以養口體,曾不知淡乎無味,非直太牢之享也。如睹高華以娛心志,曾不知見曉冥冥,非直春臺之登也。耽樂之徒皆累於物,所以去道彌遠。使其妙觀一性,則萬法皆備,即動而靜,真樂自全,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徽宗註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兄欲慮未萌,疏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疏義曰:人之有生,形體密化,其在嬰兒則性空無知,經所謂常德不離,而繼之以復歸於嬰兄者是也。孩提則親愛已兆,莊子所謂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者是也。惟嬰兄之無知,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欲慮未萌而無所思,疏戚一視而無所擇。怕兮靜止,則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和順積中而華不兆於外,則因性自然,而不假人事之華藻,故若嬰兄之未孩。蓋怕者,心無所受也。心無所受,則淡然無物,抱一守真,與嬰兒之未孩奚擇?老氏垂世立教,蓋欲使民復歸於嬰兒,是以於專氣致柔則曰#1能如嬰兒,於含德之厚則曰比於赤子,其立言雖殊,其欲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則一而已。 乘乘兮,若元所歸。 徽宗註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疏義曰:萬物之變,膠擾不齊,唯變所適,無所繫較,斯可以言乘乘。《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龍以時乘,蓋言乾道變化在乎趨時而已。惟趨時,則即彼之理,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故乘乘則因持而無所件,任理而莫之違,順物自然而不倚於一偏,故若無所歸。與所謂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同意。 眾人皆有餘。 徽宗註曰:或問眾人,曰:富貴生。食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疏義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輕其道而重其橡。聖人曰:於道行歟?眾人曰:於祿殖歟?楊雄欲救當時之弊,故設或人之問眾人,而曰富貴生也。蓋晉楚之富,富以利也,孰若保其至當?趙孟之貴,貴以爵也,孰若存其良貴?惟眾人見物而不見道,責生以肆其情,慕利以窮其欲,奢泰之心勝而侈靡者多,損約之志微而節檢者寡,故皆有餘焉,曾不知其在道曰餘食贅行。蓋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於食為餘,於行為贅,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我獨若遺。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疏義曰:聖人以道貸天下,(敕+韭)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未始有其功也。《莊子·內篇》論明王之治,有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以謂遊於無有。蓋無有者,道之妙用,聖人以至無應天下之群有,所以成帝王之功者,真餘事爾,豈認以為功而固有之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徽宗註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玆謂大智。 疏義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顏回之謂歟?觀其悟心齋之說,進坐忘之妙,聖人因其深造默識,則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所謂容貌若愚也。且一性之真,湛然常存,寂寞無為而天機不張,虛靜恬淡而默與道契,則純白內備而朝徹見獨,其為智也大矣。苟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之謂歟?然則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豈真愚哉?去小智而大智明故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徽宗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疏義曰:葆光而不露,是為明之至。行其所無事,是為智之真。流俗之情,蔽於蹇淺,繕性於俗而與之同,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非所謂明之至,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非所謂智之真。體道者異乎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遺物而不累於物,離人而不誘於人,卓然自拔於流俗之中,悟然若亡而存,如所謂湛兮似或存,悶然若鈍而利,如所謂愈鈍而後利。其迸泯,其用藏,深妙眇冥,不可測識,世俗豈得而窺之。孟子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澹兮其若海, 徽宗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疏義曰:淵乎其居,僇乎其清,淵靜而性定,內保外不蕩,澹兮其若海者,道之全體也。道之體雖不可見,即海水之大以觀之,則不以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古人之大體其實似之。 飂兮似無所止。 徽宗註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疏義曰:動而愈出,運量不匱,變動而不居,不凝滯於物,飂兮似無所止者,道之利用也。道之用雖不可見,即搖落之風以觀之,則動萬物而莫見其鼓舞之進,號萬竅而莫測其披拂之功,至無之妙用其實似之。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徽宗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眾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疏義曰:經世之道,以無用之用為至。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皆有用之用,此村之息者也。人皆知自伐其智,自矜其能,為有用之用,不知支離其德,乃無用之用焉。眾人皆有以,是為有用之用,以其村故也。我獨頑且鄙,是為無用之用,以不材故也。頑與冥頑之頑同,鄙與都鄙之鄙同。頑則不飾智,言其無知。鄙則不見美,言其無文。神人以此為不材,而不村乃所以為大材也,則無用之為用明矣。莊周於《人間世》始言曲轅社,又言商丘大木,終言桂以可食而伐,漆以可用而割,蓋明無用之用與有用之用不同如此。然則遊《人間世》 而吉凶與民同息,可不知此。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徽宗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蓄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疏義曰:道行於萬物,善貸且成,覆育無外,可以為天下母也。凡有生之氣,有形之狀,豈有須突離道者哉?楊雄著《問道篇》,有曰嬰兒慕駒犢從,以明萬物唯道之求本於性之自然,而非或使也。天道由虛靜中化出萬有,生之以遂其性,蓄之以極其養,長之使就,育之使充,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何異嬰犢之母懷乎?蓋萬物由道以生出,故道為母而物為子。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道有母之意可見矣。世之人非惟不得其母,又不能守之,捨真逐妄,道將愈遠,古人所以有揭竿求諸海之論也。若夫唯道之求者,蓋亦異於人之失性於俗者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所以為道,生而不有是謂玄德。物得以生,所以為德。道隱無名,無體可見,則非形容之所及。德有定體,有生皆全,故為人之所同得。然德兼於道,則道者所以微德之顯,故無名之道所以神其德;道散為德,則德者所以闡道之幽,故有體之德所以顯其道。能性脩反德,復乎一之所起,德至同於初,復乎泰初之無名,則德冥於道,此所以惟道是從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徽宗註曰:道體至無而用迺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2。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語道之體,未始有物,玆謂至無。語道之用,應而不窮,玆謂妙有。至無顯為妙有,此所以為物。妙有出於至無,故物無非道。道之為物,恍惚是見。恍未有狀,特心可況,故為有象之可見。忽為數始,數由此滋,故為有數之可推。恍之與惚,若有若無,謂之有而疑於無也。道之為物,其幾是歟?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徽宗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疏義曰:物生然後有象,則象者吉之先見,故見乃謂之象。四時散精為物,則物者囿於有形,故形乃謂之物。物象之具出於恍惚之中,猶如風薄千山,雷震乎天,變於大空,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化於大塊。所以成變化,故昆蟲出入草木,死生莫不待此以成。所以行鬼神,故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待此以行。道之妙,即此可見。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徽宗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疏義曰:幽在穴而難見為窈,故窈為幽之極。日藏六而為冥,故冥為明之藏。大明之上,名為至陽之原,則窈冥之中,是為至陰之原。至陰之所,於方為北。天一生水於北,在人為精。窈冥之中,所以為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徽宗註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疏義曰:精者一之所生,而天得一以清,故精為天德之至。乾之七德而言純粹精,則精為天德,可知止乎?至一盡性而無偽,是謂正而不妄,玆非至真乎?得一以生,未形者有分,是謂一而不變,玆非有信乎?若然者,萬物終始莫匪且然,而一之精通未始有間,此名之所以不去。 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眾甫之變,曰逝而不停。甚精之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眾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疏義曰: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化為神奇,眾甫之變,所以曰逝而不停。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甚精之真,所以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則得夫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之道矣。其於消息盈虛,終則有始,且有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故能閱眾甫之變,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聖人以此洗心,則常無思而寂然,退藏於密,則常無為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昔之無思者,不得不思;昔之無為者,不得不為。思出於無思,為出於無為,則高大之功,富有之業,其迹著矣。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是篇先言至精之德,終言知眾甫之然者,謂是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疏義曰: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異,大同於物,與之宛轉,宜若曲也。然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致曲如此,乃所以全其形生而不虧也。莊子以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為衛生之經,又曰外曲者,與人為徒,惟外曲則不拂人之情,玆非曲則全歟? 枉則直, 徽宗註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疏義曰:遺之使佚,宜怨而不怨。阨之使窮,宜憫而不憫。宜若枉也。然直而不律者,乃所以全其直。以訐為直者,適所以傷其義。其枉如此,是所謂直其正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蓋屈則所以求其信,玆非枉則直歟? 窪則盈, 徽宗註曰:無藏也,故有餘。 疏義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而忽已遁。藏禾於困,藏水於皿,而易已竭。惟在我者,能運而無積,然後用之需然而有餘。莊子所謂無藏也,故有餘者此也。即萬物之理以明之,窪則盈,蓋可知已。 弊則新, 徽宗註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疏義曰:能歸根,斯可以冀其芸芸。有肅殺,斯可以冀其敷榮。惟斂藏於冬者,既固然後蕃鮮於春者必茂。即四時之運以明之,弊則新蓋可知已。 少則得,多則惑。 徽宗註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為旨,則終身不解,玆謂大惑。 疏義曰:道一而已矣,故其要不煩。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惟聞見之多而能反說約,然後有得於道。若乃辨者之囿以支為旨,則多言數窮,未免乎累。大惑者終身不解,斯人之謂歟?莊子曰:夫道不欲雜。亦是意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徽宗註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 疏義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其為物不二,所謂誠也。其生物不測,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惟一能存精,惟精能集神。一者,何也?誠幾是已。一之精通,神固自全,有精而後神從之也。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抱一而已,聖人盡此矣。一而不變者,能守而勿失,則甚真之精內保而不蕩。若然則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不得已而言,言則成文而天下共由。不得已而動,動則成德而天下是傚也。《記》所謂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則,其為天下式者乎? 不自見,故明; 徽宗註曰: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疏義曰: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而無所蔽塞,故能旁燭無疆而知人情實也。不蔽於一己之見者,所以能無所不燭而為明。 不自是,故彰, 徽宗註曰: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疏義曰: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自用而嘉言是聽,故有赫赫之功,而萬邦咸寧也。不私於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者,所以能功大名顯,使天下服而能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疏義曰:經曰:自伐者無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能不伐其功,故人不爭,而其功不去。舜之命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此之謂歟? 不自矜,故長。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疏義曰:經曰:自矜者不長。《書》曰:矜其能,喪厥功。惟不矜其能,故人不爭而百姓與能。舜之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其此之謂歟?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疏義曰:眾人尚力不尚德而求勝人,故人皆取先。聖人不敢為天下先而道後其身,故己獨處後。己獨處後,則知白而守黑,知榮而守辱,榮辱一視,不以自好累其心,是謂受天下之垢。若然則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處乎不爭之地,積眾小不勝為大勝也。常處不爭之地,物孰能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徽宗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疏義曰:水之為物,因器方圓,物莫能爭。聖人動出如此,故能與物委地而全其形生,所謂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也。繩之為物,集系為之,其理常直。聖人應物如此,故能順物之枉而直在其中,所謂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也。知窪之為盈,則大盈若沖,卑以自牧矣,何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則和光伺塵,未嘗自矜矣,何夸耀之迹?凡此非知曲枉窪弊之利,強勉以行之也,若性之自為,而不知其由然虛己以應,不與物逢,以政其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則可以保身而無危疑之憂,可以盡年而無短折之息,與天地相為,長久而不知其盡也。若是者,可名為全德之人,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徽宗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疏義曰:《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德經》曰:大音希聲。希者,概而有間,非聽所聞,所謂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者也。列子言不生者疑獨,蓋不生者能生生,不生則疑於獨立,物莫能偶,所謂疑獨其希之謂歟?是以黜其聰明,而去智與故,與天合德而循天之理,巍然處其所,不從事於外,固非或使之所能為也,故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配於人乎? 徽宗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眾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疏義曰:天施地生,百昌並植,然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風以鼓舞眾形,委其自化而物得條達;雨以潤澤萬物,任其自滋而物得茂大。常因自然,非益生也。不為助長,非勸成也。故生化形色,遂于兩問,此所以為長久之道。若乃風疾轉而為飄,而雨暴聚而為驟,此非陰陽之和,乃繆戾之患,其於物也益生勸成,非因自然,物反蒙其害矣,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徽宗註曰: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迺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衛為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疏義曰:獨立于萬物之上,不從事於外者,希也。能不用聰明,默而識之於無聲之中,獨能聞和,則與道冥會,而物莫能偶矣。道至於此,無損無益,何得可名,何失可累。昧者不能朝徹而見獨,故不知獨化之自然。道本易知,而天下莫能知,於是以道為難知矣。道本易行,而天下莫能行,於是以道為難行矣。或求道於高遠,若登天而不可及,曾不知每下愈況而不拘於高也,則雖心有所係,以苦其思,能有所技,以勞其形,而從事於道,其何所得乎?以此從事,則在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道之大全於是裂矣。夫人生均有獨化,不因物而得失性者,從事於道,則吾所謂獨立於萬物之上者,復臣於道矣。雖於道德失之三等而有所得,然非自得其得也,同歸於失而已矣。 信不足,有不信。 徽宗註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疏義曰:經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也。萬物雖殊,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乃真信也。惟知道不違物,而不以道為真知,物無非道,而不以物為偽,故無往而不信矣。若夫信不足者,生乎妄見,以道為真,以物為偽,不知大全,自生分別爾,故信不足者,有不信也。若惠施之好辮,韓非之刑名,不知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而去道遠者,凡以信不足爾。 道穗真經疏義卷之五竟 #1則曰:原誤『 則則』。 #2可恍:疑為『 可見』。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太學生江澂疏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徽宗註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疏義曰:跂者支而不正,則不能疑然有立矣。跨者行之不遽,則不能憧憧往來矣。跋而欲立,跨而欲行,是不能安於恬惔、適性而止者也。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惟知率性自得,而以德為循,不矯拂以為偽,則有足者可至,若叔山無趾王駘之兀者,無所不至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徽宗註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七不足以同眾,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疏義曰:蔽於一己之見,則於事有所不燭,故智不足以周物而不明。私於一己之是,則於是有所不從,故仁不足以同眾而不彰。惟不伐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功,若有其善,則其善喪矣,何功之有?惟不矜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能,若矜其能,則其功喪矣,何長之有?惟聖人與道為一,以深為根,退藏於密,而得夫不自見之明;以約為紀,不志乎期費,而得夫不自是之彰。去泰而無泰色,未嘗自伐。去奢而無淫志,未嘗自矜。此所以聖益聖也。苟不知出此,豈所以為道乎?其於食則為餘,其於行則為贅,皆券外之所有,而非券內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徽宗註曰: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疏義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乃泰色淫志以自處,是侈於性而自盈矣,宜為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聖人不然,常以濡弱謙下為表,彼不知滿假多累而侈性以自盈,宜有道者所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徽宗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疏義曰: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三者未分名曰渾淪。渾淪之初,大樸未散,《易》所謂太極者是也。故合於渾淪,而其成不虧。《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兩儀之所受中,故天地待是以生。入於無生,則一氣渾淪而冥乎至賾;降於有生,則輕清重濁而見於有象。有生也,豈為不生之妙乎?謂之物,固其所也。 寂兮寥兮, 徽宗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疏義曰:寂然不動,則寂者未始涉于動也。太虛寥廓,則寥者未始交于物也。不涉于動,不交于物,則無聲無臭,湛然而已。 獨立而不改, 徽宗註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疏義曰:自本自根,自古固存,萬物莫能傾,萬變莫能遷,此之謂大定持之。若是則萬化無極,而道常自若,玆非道之體乎? 周行而不殆, 徽宗註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疏義曰:物出而與之俱出,物入而與之俱入,民咸用之,無往不存,此之謂利用出入。若是則一往一來,而所以常無窮,玆非道之用乎? 可以為天下母。 徽宗註曰:萬物恃之以生。 疏義曰:生者不能自生,惟不生者能生生。萬物之生,所以必恃於道也。經曰: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 徽宗註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疏義曰: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物生以水,水玆而滋者,滋也。可婁以聚,可支以散者,數也。滋者,數之先見,未至於凝形。數者,滋之已成,固囿於實體。物成數定,多寡可見者,名之所生,故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而子之,令轉生出者,字之為義,故字者滋而已。無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故道常無名。精小之微,垺大之盛,故大者對小之稱。無名則道之妙,道之妙則小而幽故也。所以字之大則道之中,道之中則大而顯故也。所以可名焉,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所謂道之妙則小而幽也。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所謂道之中則大而顯也。 大曰逝, 徽宗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疏義曰:《語》曰:逝者如斯夫,不合晝夜。則逝以言其不留,故運而不留,所以為逝。道之大,雖不外乎形數,然運而無積,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徽宗註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疏義曰:經曰:玄德深矣遠矣。則遠以言不窮,故應而不窮者,所以為遠。道之逝,雖未離乎往來,然未始有封,故逝曰遠。 遠曰反。 徽宗註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偏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疏義曰:反者道之動,則反者復乎靜,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夫道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道復於至幽,故小而與物辯。惟與物交,故可名其大,覆載萬物,一視同仁,褊覆包含而無所殊。惟與物辮,故可名以小,動者以靜,作者以息,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方與物交,則《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及與物辯,則《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道以去本為遠,其去也,運而不留,應而不窮,遠則不禦者,非與物交之時乎?道以反本為邇,其反也,歸根而靜,靜而復命,邇則靜而正者,非與物辮之時乎?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徽宗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疏義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列子所謂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則道能覆載天地矣。輕清在上者為天,及其無窮,則星辰萬物無不覆焉。重濁在下者為地,及其廣厚,則華嶽河海無不載焉。王者體是,位乎其中,達為三才,有相通之用,辮為三極,有各立之體,固能擬天地而參諸身矣。此域中之大所以有四。雖然,由非大而列為大,猶未離乎有形,自太一而分為四,猶未離乎有數,雖曰有形而不礙於形,雖曰有數而不制於數,玆其所以為大歟?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徽宗註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疏義曰:道之未降,則合於渾淪而無分,故上言混成道之。既散則囿於方體而可見,故此言域中。方未離神天之本宗,是為靜而聖,及其應帝王之興起,是為動而王。惟由靜而動,由聖而王,斯能通天地人而盡人道之極。夫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其一上比則與天同矣,蓋以王者能盡人道,能盡人道則同乎天故也。經曰:王乃天。夫王道如此之至宜乎?域中之大而與居其一也。夫然故道隱無名,獨與之遊,既與道同其體,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與天地同其功,則道也、天地也、聖人也同出一本,貫而通之,盡人而同乎天,體天而同乎道,未可以差殊觀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徽宗註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疏義曰:上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此言人法地,是以知其人謂王也。夫天無為以之清,任萬物之自滋,則不產而萬物化,斯天之神也。地無為以之寧,委眾形之自殖,則不長而萬物育,斯地之富也。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則無為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三者如此,凡以法道之自然故也。蓋人非不法天也,而曰法地,地非不法道也,而曰法天,則以語道必有其序故也。要之皆本於自然而已,故終之以道法自然。且即有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上,即非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下。有自則有他,有然則有滅,自然非道之全也,而道法之者,道出應物,其法之也降而下法故也。莊子曰:偶而應之者,道也。此之謂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徽宗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疏義曰:楊雄曰:取四重。重則不輕矣。經曰:守靜篤。靜則不撓矣。惟不輕,則物不能遷而中有所主,故不為搖奪而有所守。惟不撓,則未嘗躁進而能應群動,故不為妄動而有所制。重而有守,所以為輕根;靜而有制,所以為躁君。能自守以靜,則群動不能遷;能自持以重,則外物不能汨。失之者鮮,固其所也。凡物之行有累,則重而遲,無累則輕而速。行以輕為速,然必待輜重以自給,雖履畏塗而無中道之困,是以無患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徽宗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疏義曰: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驚散之煌煌。此榮觀所以為在物。孟子曰:四支之于安佚也。此燕處所以為在身。文王誕,先登于岸,其身安矣,然後臺沼之樂見于靈臺。身安然後物可樂,於此可見。是以雖有榮觀,必先以燕處超然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疏義曰:無為而寡過易,有為而無累難,治天下者豈可易而為之耶?禹稱堯曰惟帝其難之,湯自謂曰慄慄危懼,凡以有為者,難於無累故爾。然則有大物者,宜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徽宗註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疏義曰:貌重則有威,自然之理也,不重則不威矣。蓋君尊而臣卑,唯君尊,故不欲輕。君倡臣和,自然之分也,不倡而和則犯分矣。蓋君先而臣從,惟臣從,故不欲躁。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徽宗註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疏義曰:神無方無體而冥於道,故所存者神。化因形移易而涉於迹,故所過者化。在道者存而索至,在迹者過而不守其行,如此宜無轍迹可尋。 善言無瑕謫, 徽宗註曰: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唯聖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進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疏義曰: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同乎性命之端,而因以無窮之變,則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為言若此,宜無瑕謫之累。且自《易》觀之,象為天下之至賾,君子則擬象而言;爻為天下之至動,君子則議爻而動。言行存乎人,變化在天地。言行始于擬議,而終于成變化,則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惟聖人得言之解,為行之宗,可以為千里之應,可以政天地之動。變化之妙,其成在我,如是而行,則行而無迹,獨往獨來,惟大方之蹈,尚何轍迹可尋哉?如是而言,則言而當法,設之以神,無斯言之玷,尚何瑕謫為累哉? 善計不用籌筭, 徽宗註曰:通于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疏義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以天下之數皆生于一故爾。能通其一,故萬事可畢。既已為一,乃麗于數,麗于數者,猶可以知萬,況不麗于數而能生數者乎?宜其不用籌畫計筭,萬變之殊雖若甚眾,而若數一二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徽宗註曰: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塞兌閉門,執神而固,物不能易其真,塗那守神者然也。莊子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幾是已。眇阜深根,晦位冥畛,而世不能窺其迹,退藏於密者然也,莊子言藏乎無端之紀,幾是已。以是處己,雖無關楗,孰得而開之?夫是之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徽宗註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然,一性之真是已,與生俱生,確乎不拔,豈待繩約而固哉。待繩約而固者,是戕其真而散其樸也,故為削其性。善結者不然,沃人之心,本乎至和而無俟於言,正容悟物,使人意消而不假於勢,莊子所謂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正此意也。若然,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徽宗註曰:善者道之繼,冥於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于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惔寂寞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疏義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故善為道之繼,復乎大道之原,則善之與惡,蓋將簡之而不得,故無善之可名。散為可歌之善,則本之以道而善兼天下,此善名之所以立也。自善行以至善結,聖人所以有此五善,至於人物無棄,在乎能體道以濟天下故也。夫聖人愛人而救之,使人樂其生,利物而救之,使物遂其性,曾何容心哉?反一無迹,循道而不違,因其常然,乘禮而不迕,任萬物之官生,百姓之自治而已。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無以興乎世,故民失其恬惔寂寞之性,樊然殺亂,菁然疲役,日淪於憂患之域,不有以在宥之,安能使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哉?非職教化者,以道任天下之重,出道善世,俾民物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能成善救之功哉? 是謂襲明。 徽宗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疏義曰:龍之為物,能見能隱,襲則隱而未見也。以隱也,故衣在內,則襲有不表而出之之意,與惕襲不相因之襲同。襲明則圖滑疑之耀,去形謀之光,不自用其明故也。聖人之於世,豐智源而音出,眾人昭昭,我獨若昏者,為是故爾,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已。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徽宗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疏義曰:凡利之路,可化以為貨,可有以為賄,資之為利,利之次也。故資以言其利,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爻以自省,則有不善人,然後善人之功利著,此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是意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徽宗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疏義曰:論性之本,善否一玫。自常人言之有善也,不善為之對,自聖人言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其心空然,初無去取。彼不善人之師,夫何所貴?彼善人之資,夫何所愛?彼是莫得其偶,兩忘而化於道。知夫善惡之辨生乎妄見,夫何剪剪分別而生貴愛之心哉?大同於物,於聖人見之。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徽宗註曰:道之要妙,不睹眾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疏義曰:善者,離道而為之也。智者,道出而生之也。道之要妙,冥善惡於一致,故不睹眾善,以智索之而不得,故無所用智。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此所以大迷也。昔者黃帝將見大魄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而方明滑稽之徒,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蓋大魄則道之要妙之譬也,七聖則未免乎用智之譬也。七聖皆迷,無所問塗,則以見道之要妙不可以智知矣。莊周之書,與老氏相為表裹,蓋見于此。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徽宗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雄,陽物也,體剛而乘物,故能以剛勝物。雌,陰物也,體柔而承物,故特柔靜而已。聖人之智,威可以服海內,力可以旋天地,則知所以勝物矣,是為知其雄也。然雖剛也,必況潛而處乎柔;雖動也,必深密而處乎靜,是能守其雌也。惟處乎柔,故能不絕物;惟處乎靜,故足以應群動。既以與人己愈有,德澤洋溢,未始有匱,是所以為天下谿之也。且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之,則谿下地宜為流水所赴。聖人守雌以柔靜,受萬物而不辭。且壯以有立剛克之事,執謙之柄柔克之事,聖人於剛則沉潛,故不用壯,於柔則立本,故持之以謙。不用壯而持之以謙,是乃知雄而守雌也。德出於性,初未嘗離,一於剛則焚其和,一於柔則無以立,惟知雄而有其剛,守雌而濟以柔,則成和之修,充於所性,天渾然成,斯為全德之人矣,其與嬰兒也奚擇?蓋嬰兒氣專志一,故和而不暴,欲慮未充,故醇而未散,惟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復歸於嬰兒也。孟子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與此意同。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徽宗註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猒,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 疏義曰:白陰之中,於方為西,萬寶既成之所,故以況德之著。黑探其本,於方為北,萬物歸根之時,故以況道之復。聖人發乎天光,照臨下土,則自昭者一性之德,是為知其白。退藏於密,不出其宗,則默會者又本乎道,是為守其黑。道德純備,無有一疵,故有則可則而天下是則,有效可傚而天下是傚,無思不服,樂推於當時,盛德難忘,不猒于悠久,故為天下式也。惟為天下式,故其正則止一而不遷,其時則相因而必至。正而不忒,未始有妄信矣,不期如彼,四時德至於此,何差忒之有?若是者,真精之原同乎天倫,孰要其所終?孰知其所窮?蓋萬化而未始有極,玆所以為常德不武歟?雖然《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歸於無極者,何也?蓋《洪範》之作,箕子所以闡道之妙;《道經》之作,老氏所以微道之顯。闡道者,以道中庸為主,故云有極。蓋德之見于事,以中為至也。微道者,以極高明為主,故云無極。蓋德之復乎道,不可致也。極,中也,猶屋之有極,眾村之所會,猶天之有極,眾星之所共。或有或無,各有所當而已。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徽宗註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迺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疏義曰:一性凝寂,至虛而已。自券之外,無適非妄,則性分之外皆為物也。然世之人得之若驚而喜,失之若驚而憂,此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也。或充訕於富貴,或隕穫於貧賤,此以泰為榮,以約為辱也。聖人知夫物之來不可拒,故不以得為榮,其去不可止,故不玖失為辱。榮辱一視而無取拾之心,遊於券內而不志乎期費,內保不蕩,而以約為紀,極天下之至虛,而無一毫之攖,故為天下谷也。蓋谷之為物,虛而能受,受而不藏,虛而能應,應而不竭。在我之德,其虛若此,故能應天下之群實,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玆所以為常德乃足歟?虛靜之中,有物混成,道之體也。木之為樸,未散為器,其質全矣。道之全體乃在於此,能復歸於樸,則明於大本大宗,是為能備道。雖然,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之貴自以為稱,凡以明道而知貴之本也。抱樸則得其道矣,得道者多助,故天下賓,抱樸而天下賓,經所謂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樸散則為器,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疏義曰:超乎太極之先者,道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未離方體之內者,器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與器,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自道言之,則大易未判,有物混成,故全,天與人合而為一。自器言之,則大樸既散,隱顯既分,故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徽宗註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所謂道之全,聖人以治身也。道之土苴以治天下,所謂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也。惟散道以用天下,則舉而措之者有分有守,其形可見而其名可言;有形有名,其能可因而其材可任。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矣。莊子論大道之序,言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繼之以必分其名,必由其名,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義與此合。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於此可見。《易》言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道德全備,仁義兩得,足以為萬夫之望,官長之謂乎? 故大制不割。 徽宗註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彫眾形,而不為巧。 疏義曰:因形移易謂之化。離形頓革謂之變。由化而至於變,道之序也。聖人知變化之道,而兆於變化,制物而不制於物,如《易》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者也。然雖制物而無辨物之迸,刻彫眾形而不為巧焉,所謂方而不割者也,非大制未易至此。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強,殆謂是歟。 疏義曰: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是雖天下之廣,可名以大物。然不通乎道,雖有大物不可以物物矣,惟夫與道為一,而不物于物,則可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能物天下之物也。蓋留動而生,莫逃乎物,必有不囿於物,而能物物者。物物者,道也。能明乎道之非物,則宇宙在乎手,而無以天下為,可以膺天下之寄託矣。莊子所謂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終之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正此意也。雖然,天下大器不可為也,不明乎道,取天下而為之,是用智而恃力也,用智則智必有所困,恃力則力必有所殆,其於道,失之遠矣。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者,凡以道化不物於物,而智力以囿于物故也。惟不物,故能物物,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也。彼嬴秦徒以智力為尚,豈足以治天下哉。故古人以為秦失之強也,楊雄以秦為狼,亦以是爾。 天下神器, 徽宗註曰: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問,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 疏義曰:謂之六合,則制於形數矣。謂之宇宙,則囿於方體矣。域於覆載之兩間,而非覆載天地者,故天下雖大,謂之器焉。然立乎不測而莫見其進,行乎無方而未始有封,為之而不知無為,則必敗,執之而不知趨時,則必失。雖未離乎器,其為器也,可謂神矣。 不可為也。 徽宗註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疏義曰:有形則可名,有分則可守,所謂器也。必有不器者,然後能運其器。不器者即不物於物者也,惟不物於物,則萬物雖多,群動不一,皆不出防範之內,雖不期於宰制役使,而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矣。凡以明乎非物而能物物,故無為而天下功也。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固以治矣。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莊子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南面而君天下者,苟執於事為之迹,而不知以無為為常,以有涯逐元涯,則智有所困,孰能用天下而化萬物哉?故莊子曰多知為敗。 為者敗之, 徽宗註曰: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敗。 疏義曰:入而與物辨,則不同,同之斯無為也。出而與物交,則有所別矣,不得不為也。不得不為,則彼是戾矣,能無敗乎?惟夫以無為為本,以有為為末,無為而無不為,則應物有裕而不匱智,孰有所困哉?廣成子曰多知為敗,則以無知,故能無不知也,何敗之有? 執者失之。 徽宗註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疏義曰: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時徙不留,道亦應變,則道之所貴者時也。物無常宜,宜在隨時,苟執而不失,泥於一曲,失之則過,後之則不及,能無失乎?惟與時俱化,而無有專為,則於時不失,於道不違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羸。 徽宗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疏義曰:曰往則月來,日月遞照,未常停也,物理之或行或隨如此。春先而夏從,四時相代,莫或已也,物理之或噓或吹如此。木壯則水老,火生則金囚,物理之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如此。禾死而麥生,木隕而鞠華,物理之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如此。自行隨以至載隳,皆為時所役,故與時終,為數所制,故與數盡,是以循環往復而未免乎累。若夫超于時而不與時終,離于數而不與數盡,何累之有?聖人解乎此,體道之無,故不累於物,體道之尊,故獨立于萬物之上。道之在我,物不能偶,如是而往,則無所因而往,故為獨往,如是而來,無所從而來,故為獨來。莫之爵而常自然,可謂至貴矣。不物之妙,乃在乎此,豈有為者之敗、執之者失哉?宜其運神器而有餘裕。夫聖人心超有無,不累於物,故事變交錯而我法不遷,此所以物態不齊而心常一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徽宗註曰:聖人睹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執,敗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疏義曰:物壯則老,故有變遷。滿則招損,故為多累。聖人知行隨、噓吹、強羸、載隳返復不一,是能睹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因其自然而無益生,以約為紀而無泰,至內保外,不蕩而無侈性,是所謂游乎券內者也。游乎券內者,行乎無名。無名者,道也。所行在道,豈有甚與奢泰之患哉?守其性源,與道宛轉,其治天下,體乎無為,故無為之之敗,合乎至變,故無執之之失。彼繁文飾貌者,方且累乎甚與奢泰之患,其何益於治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太學生江澂疏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徽宗註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疏義曰:莊周論治言五末,而三軍五兵之運,於德為末,所謂本則精神心術是已。兵不可偃,故五末者,古人有之。君子務本,故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蓋優於為君子矣,豈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以威服天下哉。昔梁惠王願比死者一酒齊楚之恥,孟子告以仁者無敵,夫豈以兵強天下哉。 其事好還。 徽宗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疏義曰:出於己者善,則人亦以善報之,出乎己者不善,則人亦以不善報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苟以好攻戰為心而樂殺人,則其報之以類當如何哉?以其事好還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凶年。 徽宗註曰: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疏義曰:耕無鹵莽,耘無滅裂,是謂人力。雪則優渥,雨則霑足,是謂天時。用兵則非所以力地力,至於奪民力,故荊棘生焉,非所以召和氣,至於上違天時,故有凶年焉。《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與天地通乎一氣,故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此講武之詩,與老子不同者,以明聖人之志異乎人之武志歟。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徽宗註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眾。 疏義曰:事雖不同,均欲求可;功雖不同,均欲求成。然有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寡者,不知秉本據要而已。聖人之道,天下之本,與夫為治之要在是焉,故用力少而見功多。若夫覿武觀兵,以強勝人,豈德之吉者哉。先王用兵,固有常勝之道,然有左旋右抽而事功罔濟者,不知聖人之道故也。聖人之道,故在和眾而使之同心協力,則事無不可,功無不成,而無敵於天下,左氏所謂師克在和不在眾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苟卿曰:士民不親,雖湯武不能勝敵。然則師克者,固在和不在眾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徽宗註曰:綠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疏義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則出應帝王,豈得已哉,況用師乎?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若師之九二是矣。體順行險,履中問罪,如田而有禽,此所謂以中而吉也。柔而得正,能以眾正利,執言而無咎,此所謂以正而無咎也。然聖人用師,豈窮兵黷武,以逞無饜之歌耶?緣於不得已,而不寧之方斯懷來矣。若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豈善持勝者乎?蓋殺敵為果,能果而不矜,則天下莫與之爭#1,能果而勿伐,則天下莫與之爭功,能果而勿驕,則功成不居,是以不去。故事功之成,世莫得而競也。 物壯則老, 徽宗註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疏義曰:有春夏之長養,必有秋冬之肅殺,大化密移,疇覺之哉?物壯則老,此可見已。 是謂非道, 徽宗註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疏義曰:其始無首,孰原其所始?其卒無尾,孰要其所終?自古固存,化化而非化之所能化,故道不與物化。道之與物相去遠矣,故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非道早已。 徽宗註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疏義曰:囿於大化之中,方剛而為壯,既衰而為老,物皆然也,凡以外乎道故爾。道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豈有老壯之異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徽宗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疏義曰:物類之起,必有所始,福之將至,有開必先,自然之道。福之兆乎物謂之祥,故《易》官吉事有祥。兵,凶器也,尚何吉之先見?所以為不祥。雖然,黷武類禡,動惟厥時,雖先王所不廢,然匿文者不昭,故必耀德,黷武者無烈,故不觀兵。《傳》所謂兵戢而時動,蓋謂是也。武王戢干戈而棄弓矢,求懿德以肆時夏,玆耀德不觀兵也。且武之為義,冠卷取之以其隱而不觀,足進取之以其棄而不用,宜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徽宗註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疏義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故左為陽而右為陰。陰陽者,生殺之本始,故陽主生而陰主殺,德主生,故管子以謂陽為德,刑主殺,故管子以謂陰為刑。德成而上,物莫能賤,是以君子貴德。刑之將用,為之徹樂,是以君子畏刑。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徽宗註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疏義曰:兵者,不祥之器,雖有道者不處,然聖人應世,將以安民,則暴者不得不禁,亂之起也,不得不救,不庭之方來干天討,則兵戢時動,不得不往。夫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用之,豈本心哉,緣於不得已爾。是以常處不爭之地,而不敢為天下先,豈以勝物為心哉?以恬惔為上故也。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徽宗註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首,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疏義曰:仁者無敵,故國君好仁,則天下無敵焉。不明乎此,至於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是安其危而不以為險,利其苜而不以為害,樂其所以亡而不以為不美也。是宜怨之所構,禍之所集歟?又烏知王者之兵,本以仁義,行以征罰,有事則討,無事則已,以為常安之術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徽宗註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疏義曰:在《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王者之兵,所以容民蓄眾,雖戰而勝,猶醫師聚毒藥以攻疾,必有被其毒者,故《易》以師 為毒天下,而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微宗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疏義曰:無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者也,故不得而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徽宗註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疏義曰:莊子曰:同乎無欲,是為素樸。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所以喻道之全體,大者在上,寡而勝物,小者在下,眾而物勝,自形名而降乃如此。若夫道之全體,不立一物,搏之不得,名之曰微,與性圓融,復乎至幽,可名於小矣。是道也,不麗於體,不囿於數,真君足以高天下,非若域於方體而以大為累者,此所以天下莫敢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微宗註曰: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疏義曰:《語》曰:何莫由斯道也。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蓋道者,似萬物之宗,而萬物莫不尊道。苟能守道,物所以賓也。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樸則道之全體,體道故民性得,其意正與此合。在《易》之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然則服萬物者,何俟於威刑哉?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徽宗註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疏義曰:純則不虧其神,素則無所與雜。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勿失,則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豈特賓物而已哉?仰合於天,則上與元化交,俯參於地,則下與厚德並,精神四達,上際下蟠,與天地同流,則兩者交通成和,而甘露降矣,物孰有不被其澤者哉?蓋甘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生,聖人純素之道格于上下,而天地之和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鶡冠子》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蓋天無為以之清,上及太清,則上際於天也。地無為以之寧,下及太寧,則下蟠於地也。惟人萬物之靈,中及萬靈,則及乎萬物也,此甘露所以降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徽宗註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息,不七之人,次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疏義曰:莊周論九變,自明天第之至形名而其數五,有形可名,則去道德遠矣,故道降而德衰。離道既遠,則樸散為器矣,故澆淳散樸而莫之止。是以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息,不仁之人,次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蓋蒿目則視之不明也,惟不能內視為明,故常憂而不樂,所謂七則反愁我身也。不仁之人見利而忘真,次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所謂責者常憂不足也。蒿目而憂世之息,則若枝於手而有餘於數之類也;央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則若駢於拇而不足於數之類也。聖人不然,於始制有名之時,則塊然獨以其形立,豈隨物而遷哉?澹然獨與神明居,豈不足為息哉?正以止之,固以執之,於流能止,即動而真,若是,孰能危之?所以不殆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徽宗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往,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疏義曰:有生不同,同稟一性。凡以有生,斯有性爾,則天下一性也。道之全體,不離於性,聖人得其純全,故有性者皆以性合,猶江海善下之而百川水潦歸焉。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往垂拱而天下治,夫何為哉?因民之性以化之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徽宗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疏義曰:瞧螟秋毫,物之至微者也,雖百步之遠,善視者猶能見之。人之眉睫甚邇者也,雖使離朱當晝拭訾望之而不見焉。人之為智蓋亦如此,則以智可以知人,而不能以自知故也。韓非載杜子之言,以謂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蓋謂是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苟子曰:是是非非之謂智,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矣。所以為智之事然而如目焉,可以見外不能自察,但可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徽宗註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曰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鎰也,萬物之照也。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返本而靜,靜則明,無不燭,故《易》曰復以自知。內視則於見無愛,不見彼而自見,故《傳》曰內視之謂明。用智以察人之邪正,則提是而排非,四顧而物應,是為與接為構,以虛一而靜之心日校。夫是非之正,是為日以心鬬,此特知人之事而已。若夫復以自知,則內觀一性,靜而返本,視人之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而得其所謂見見者焉。天地之大於此乎?見是其鎰也。萬物之多於此乎?形是其照也。若然,則其為明,果有既耶?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徽宗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疏義曰:愚者不足與有謀,故智者施其察而詐愚;怯者不足與有敵,故勇者奮其恢而苦怯,此尚力而勝人者也。勝己之私而用心剛直,養無害而其氣完,此尚德而自勝者也。夫惟自勝,則外物交至,不足以喪吾存,故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逐世無悶。夫獨立若可懼也,今乃不懼,是為勇於義。遯世若可悶也,今乃無悶,是為安於命。或出或處,無往而不勝,玆其所以為至強歟。 知足者富, 徽宗註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疏義曰:萬化之生,其名不同,有而不失,是為至富,則以至足之分存乎吾身也。莊子所謂有萬不同之謂富者,此也。惟知足之人,游乎券內,取足於身,故首圓足方而天地位,胸南背北而陰陽該,有物有則而萬物咸備,晉楚之富,豈足以為之比哉?知足之足,常足,此所以國財并焉。 強行者有志。 徽宗註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疏義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曰起而大有功。故有為者在於自強,而自強者是為有志。《德經》曰:上士聞道,動而行之。蓋士志於道者也,聞道而動行,則真積力久而自強不息,非有志者能之乎? 不失其所者久, 徽宗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疏義曰:人能體常不變,一於所守,斯能放道而行,悠久無疆,在《易 之《但》,其象言君子立不易方,而象以謂聖人久於其道,正此之謂。彼時徙不留,與之推遷,物有壯老,與之轉徙,果能不失其所者乎? 死而不亡者壽。 徽宗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于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疏義曰:凡物生為出乎一,死為入乎一,生有所萌,則出乎一也,死有所歸,則入乎一也。原始而知死之說,若莊子言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今又變而之死之意是也。反終而知生之說,若莊子言吾又安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薪生之意是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則死生之說豈有異耶?一以貫之而已。蓋一昏一明而晝夜分,流形於天地之閒,而從役於晝夜者,凡物皆然。晝夜相承,猶之死生相代也。彼囿於時數,而與物相轉徙者,固未免晝夜之所躍矣。惟達者知通為一,以死生為一條,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有所謂不往,知死之未始異於生,彼形體萬變,與時俱化,而真性湛然,其神不亡,則以通乎晝夜而知獨得,夫所謂至一,故天長地久而與之俱為無窮,其為壽也,蓋莫知其極矣。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蓋窮理則不蔽,故知人為窮理;盡性則無欲,故知足為盡性;達命之情則命萬物而無所聽,故死而不亡為至於命。《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序與此篇之義同。惟至於命,則造化之妙皆自我出,朝徹見獨,與道冥會,超於時數,而古今之所不能囿,離於形體,而死生之所不能役。莊子言無古無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此之謂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徽宗註曰:汎然無所繫輆,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疏義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左為陽,右為陰,故汎然無所繫輆,可以左右也。《太玄》曰:無所繫輆者,聖也。莊子曰:有左有右,惟無所繫輆。故不膠於一方,而有左有右也。若然則動靜在我,若陰陽之消息相為盈虛,何失之有?則動靜不失矣。往來在我,若曰月之遞照相為晝夜,何窮之有?則往來不窮矣。取之左而左,取之右而右,無門無旁,四達皇皇而莫不達其原,烏乎存而不可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徽宗註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疏義曰:往者資之,莊子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也。求者與之,莊子所謂至無以供其求是也。惟其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而無所辮,故生化形色,智力消息,一付之自爾,何尸其功哉?譬如四時,戊出則丁藏,木壯則水老,功成者去,豈認而有之哉?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徽宗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辯,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眾,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疏義曰:精入乎神而么,景出乎明而大,故復於至幽為小,顯於至變為大。天道升於北,則復之時也;降於南,則離之時也。南交而北辨,故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則物我兩忘,故常無欲;與物交,則與物委蛇,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自其在己者言之也。鼓舞乎群眾,而莫窺其歸往之邇,故不知主,自其在人者言之也。且道覆載萬物,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故於覆露萬物言不示其宰制之功,惟不示其功,則不為之主矣。鼓之舞之以盡神,故於鼓舞群眾言莫窺其歸往之迹,惟莫窺其述,則不知所主矣。蓋道不在大,亦不在小,則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非真常也,道之及乎物者爾。及乎物,則非形而上者之道。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疏義曰:有大美而能遜,故能有其美。有成功而不居,故能保其成。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蓋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未離乎有形,形之大而不能化,未免乎有敝。惟變動不居,故成名於聖,而無為大之累。無為大之累,則不自大矣,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徽宗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律,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疏義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垂象,運而無積,周行不殆,其行健矣,果何為乎?莊子曰:無為為之之謂天。《易》曰:天行健。此無為而運之以健也。曰星回旋,雲霓伏見,其文見矣,然天何言哉?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易》曰:仰以觀於天文。此無言而示之以文也。聖人之御世,體天道之變化,執大象以示人,如天之垂象,處無為之事,雖為未嘗有為之之邊,行不言之教,雖教未嘗發言之之意。故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其好我也,親若父母,附離不以膠漆而固矣。故言執大象,天下往。其曰大象,則以若可見,不可得而見也,經所謂大象無形是已。 往而不害, 徽宗註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疏義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陰陽和靜,列子所謂陰陽常調是也。以道往天下,故鬼神不擾,列子所謂鬼無靈響是也。以遂群生而群生連屬其鄉,故群生不傷,列子所謂人無夭惡是也。以育萬物而萬物各得其宜,故萬物不夭,列子所謂物無疵癘是也。妙而為陰陽,幽而為鬼神,眾而為群生,散而為萬物,無不處其宜,此之謂至一,故能常使民無知無欲。民雖有知,無所用之,天下之大利,於此致焉,何害之有? 安平泰。 徽宗註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疏義曰:安者危之對,故安則無危亡之憂,所謂天下常安也。平者陂之對,故平則無險陂之患,所謂天下均平也。泰者否之對,泰者施澤及下之時也,故《易》言泰者通而治焉。自安以至平,自平以至秦,治效如此,非執古道以御今之有,孰致是哉? 樂與餌,過客止。 徽宗註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疏義曰:屬其性於五聲,故耳欲茶聲,而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屬其性於五味,故口欲綦味,而五味嗎。,使口利爽。則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故也。累乎物,故內外之韄其繁且繆,莫之能解矣。然其不能自解者,以不知疏通開達,物有結之爾。是雖過客之不遑啟息,亦為之止矣。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徽宗註曰: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疏義曰:天有五行,化生五味,始於淡,窮於甘,皆味之所味也。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其曰味味,莊子所謂天下之正味是也。彰為五色,或探其本,或質其物,皆色之所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其曰色色,《易》所謂貴無色是也。別為五聲,清濁高下,達回侈拿,皆聲之所聲也。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其曰聲聲,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信言不美,故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而能味天下之味。易無形好,故視之不足見,而能色天下之色。無聲無臭,故聽之不足聞,而能聲天下之聲。味天下之味,則能甘能苦矣;色天下之色,則能玄能黃矣;聲天下之聲,則能宮能商矣。無味也,不足見也,不足聞也,疑若無知無能也,然而能味味,能聲聲,能色色,運量不匱而其用不窮,則無不知,無不能也。是以列子論形生聲味,而終之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故曰用之不可既。《傳》曰:無聲而五音嗚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其斯之謂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發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徽宗註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僨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睹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疏義曰:陰陽之運,曰往月來,有以相照,下與上騰,有以相蓋,一消一長,有以相治,此陰陽相蓋相照相治也。四時之行,寒暑推移,有以相代相生相殺之繼,王有以相生,壬之剋勝有以相殺,此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以至散為萬物,其理不說,序為人倫,其傳不息。斂者萬兆,而散者已萌,則或歙或張然也。盛者未已,而衰者俄繼,則或弱或強然也。以至一憤一起而廢興更代,一虧一盈而予奪迭用,發於未萌,藏於未兆,雖有神視,莫觀其形,幾常發於細微而莫睹其朕。惟聖人見曉於冥冥,而作炳於絲忽眇綿之上,能極深而研幾,則以得先見之吉也。賢者雖不及於知幾,然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殆庶幾乎。今夫積陽成暑,則陽盛於夏也,然子美已盡,而陰且生矣。積陰成寒,則陰凝於冬也,然午美已極,而陽且生矣。楊雄所謂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也。是皆歙張廢興、迭運更化之所致焉,此在天之理也。句踐欲弊吳,將欲弱之也,而勸之伐齊,必固強之也。智伯欲襲仇由,將欲奪之也,而遺之廣車,必固之也。韓非亦曰:晉獻公將襲虞,遺之璧馬。智伯襲仇由,遺之廣車。以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亦是意也。此在人之事也。稽諸天理,驗諸人事,莫不皆然,此聖人察象識類,於陰始凝,履霜而知堅冰之至也。故能於天下之理一消一息,一滿一虛,不位乎其形而察夫形形者,彼其理雖未兆,昭然而可睹矣。若然,則歙張強弱廢興予奪制之自已,運之自已,勇者不敢奮其恢,其強不能弱,智者不敢施其察,其守不能奪。與天為一,而天道已行,唯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能與於此。 是謂微明。 徽宗註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楊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睹而眾莫知。 疏義曰:涉於有進則顯而易見,藏於未兆則隱而難知。歙張強弱廢興予奪相為消長,相為倚伏,方其未兆則深妙眇冥,視之不見其進,閟隱而難知也。自理觀之,盛極則衰,窮極更生,迭作不停,雖藏於無朕,而必至之理昭然而可見,則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矣。楊子作《太玄》有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睹而眾莫知。蓋水幾於道,周流無際,損於此者必益於彼,虧於此者必盈於彼,則水雖息於淵而木已消於枝矣。眾人求其述,賢人造其理,故賢人睹而眾莫知,眾人則異賢人可見於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徽宗註曰: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猶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輩大屋者,惟我能也。 疏義曰:自事言之,剛強足以勝柔弱;自道言之,柔弱足以勝剛強。柔勝剛,弱勝強,以道言之也。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得常勝之道歟?莊子所謂積眾小不勝為大勝,惟聖人能之,此之謂也。且自道而降,幾於道者,惟水為然,而水性解緩,是為天下之至柔,而能攻天下之至堅,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是也。至於風亦然,巽入為用,撓萬物莫疾乎此,亦以柔弱勝剛強也。《莊子·外篇》論蛇風相憐曰:指我則勝我,猶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輩大屋,惟我能者。蓋指我、我、勝我,所謂柔弱也。折大木、輩大屋,所謂勝剛強也。《傳》曰:柔者道之剛,弱者道之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徽宗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場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薪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疏義曰:淵,水反流全一,水之深而難測者也。魚潛逃隱伏,不猒深渺而已,則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也。利器,人主之至權,所以宰制萬物者也。故勢在上,則臣制於君,則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也。然魚之在水,猶人之在道,人不可須突離道,則魚不可須臾失水。吞舟之魚暘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以脫於淵故也。賞罰者,勵世之見,人主自用之,則群臣畏威而服利。於賞善而不周密,是君見賞也,人臣則用其勢矣。於罰惡而不周密,是君見罰也,人臣則乘其威矣。夫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已。韓非亦曰:賞罰者,邦之利器。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盜之以為威。亦是意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矣。夫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有,有妙道存焉,所以能運神器而無執,有大物而不失。能窮海內而無智力,非無智力也,智力之所用,人無得而名也。威服海內而無勇功,非無勇功也,勇功之所施,世無得而睹也。若然,則非有心於勝物,而拘拘為是也,不薪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焉。得道之弛張,而陽開陰閉,《傳》所謂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是也。知神之所為,而變化無窮,《傳》所謂兆於變化是也。以之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制人而不制於人,非善持勝者,能若是乎?此無他,本在於上,正其本而萬事理;要在於主,得其要而萬事治。不治天下,而天下固已治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徽宗註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無為其體也,無不為其用也。一於無為以求道,則溺於幽寂,失道之體。一於無不為以求道,則滯於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動,無為而不廢於有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不為而不離於無為,則道之至妙無餘蘊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徽宗註曰:鎰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于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明燭鬚眉。鎰之與水,應而不藏,人所取監也,故《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道之應物,何以異此?得此者,上為皇,下為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未興事造業者,王之道。制節謹度者,侯之事。則侯王者,萬物之所係也。誠能守道以御時,其於治天下國家有餘裕矣。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土直以治天下。惟能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意其有為而未嘗有為,意其無為而未嘗不為,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不為,以是化貸萬物,則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莫不得於觀感之際,而其化均矣。猶一氣港運,大化密移,芸芸職職,自生自殖,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自化而已,此何與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僿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偃,故民惟上之從。所謂上之化下,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也。暴悍勇力者,化而愿;旁僻曲私者,化而公;矜糾收繚者,化而調,因形移易而未免有作也。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道之全或虧;險德以行,而德之體或失。蓋道無善無不善,繼之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成德為行,則不易而險矣。道與德皆性也,善與行則性之發於心者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則是去性而從心也。以心定天下,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矣。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無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囿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恌薄之患哉?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徽宗註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袪其惑,解其蔽。 疏義曰: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則季真之莫為,猶在物一曲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少知有二家之議,以發問於太公調也。雖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天地則無為而為之也。無名之樸,若季真之莫為也。莫之為則寡能備天地之美,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袪其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惑,其見於此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則正#2,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疏義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以上善若水,幾於道故也。水之為物,方圓曲直,雖趣變無常,及其靜也,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所謂莫動則平,與夫主量必平是也。道之體如之,古之人所以有取於水也。蓋水靜則平中準,則不欲以靜也,大匠取法焉,則天下將自正也。不欲以靜則一而不變,不失其正矣。不失其正而先自正,是為正己而物正,故天下將自正也。莊子所謂幸能正生以正眾正,惟止能止眾止,正此意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離形頓革謂之變,因形移易謂之化。乾道見於變化,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且然無間謂之命。萬物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此篇始言道常無為無不為,終言天下將自正,政治之效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此之謂治之至。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竟 #1莫與之爭:此句疑有脫。 #2不失則正:『則』疑作『其』。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太學生江澂疏 徽宗註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疏義曰:通變之謂道,則道不可以方求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則道不可以體求也。蓋道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無方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寶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得見,是無體也。道無方體,果且有成與虧乎哉?德有定體,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蓋德有上下,惟知崇之,然後能進而上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德有小大,唯知修之,然後進而大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莊子曰:德成之謂立,則德固有成也。又曰義可虧也,則德固有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合于道,無德之可名,楊雄所謂合則渾,莊子所謂德總乎道之所一也。自其異者視之,則別乎德,有名之可辨,揚雄所謂離則散,經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是也。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履此,智以知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職其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隨量而受,各得一焉,因時而施,是德而已。若夫道則不然,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周流彌滿而無或缺,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孰有成虧之異哉?體道者異乎德如此,故德列于下經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疏義曰:原始言之,則生非德不明。要終言之,則生者德之光。墮於域中,莫不有生,而物之所以生者,得一故爾。一者何也?德幾是已,莊子所謂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均有德,則同焉皆得矣。德兼於道,則默與道會矣。惟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循理而動,因時而為其過也。非有心於過也,理之不得不過爾,孰為悔?其當也,非有心於當也,理之不得不當爾,故不自得焉。真人之德如此,是謂不德。若然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謂上德矣。昔孔子以天縱之將聖,於答公西華之問,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於答子貢之問,則曰聖則吾不能,固不居其聖矣。然而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集三子之大成,孟子以為聖之時,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有德可知已。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徽宗註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疏義曰:道之在我,未始有物,擅有於道,道將汝失,然則認而有之,皆惑也。且自營為私,背私為公,道者為之公,擅有於道,是自私也。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則自私豈不失道乎?欲不失德而乃無德,非下德而何?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徽宗註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疏義曰:一性有覺,洞徹無窮,不思而得也。用之不動,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也。未嘗用力,無往不存,不行而至也。若是則出為不為,而為出於無為,德之盛無以易此,故曰上德。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徽宗註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疏義曰:自誠而明謂之道,自明而誠謂之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自誠而明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勉之則中,不勉則不中;行之則至,不行則不至,自明而誠也。自誠而明,聖人之事,自明而誠,賢人之事。德有上下,聖賢之所以分歟?不累於形,不鑿以智,而離形去智;形不能礙,智有以徹,而通於大同。忘仁義,忘禮樂,仁義禮智,蓋將簡之弗得,而未始有物焉,是之謂無以為,此上德也。澶漫為樂,摘辦為禮,而屈折禮樂,整躉為仁,踶跂為義,而吁俞仁義,用是以慰天下之心,適足以攖天下之心,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是之謂有以為,此下德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徽宗註曰:堯舜性之,七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疏義曰:莊子曰:大仁不仁。所謂不仁非無仁也,能仁而無以仁為也。故有所謂安仁,有所謂利仁。安仁則由之而無以為,利仁則以仁為利而行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安仁而非行仁之謂也。故仁覆天下而無不被,此之謂上仁。莊子言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書》稱帝堯之德而曰安安,此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徽宗註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疏義曰:義主辨則列敵者義也,義設於適則度宜者義也,楊雄所謂列敵度宜之謂義者,此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義不可勝用,則義固立我矣。苟子曰以義應變,則義固制事矣。惟其立我,故《字說》 曰義者我也。惟其制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立我而不能忘我,制事而不能棄事,皆涉於有為矣,非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者歟?鳧鹥之詩於公尸來燕來宜,而繼之以福祿來為,則以來為者為其有義故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徽宗註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息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疏義曰:辨則用戈,交則用豆,禮之於賓主,用豆之時也,則禮以交物矣。升降上下,周旋禓襲,禮之寓於文,自外作也,則禮以示人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實在於事親,義之實在於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禮以節文仁義矣。經禮至於三百,曲禮至於三千,自吉禮以至嘉禮,自天神以至人鬼,其用多矣。要而言之,莫先施報而已,《記》所謂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也。然禮尚往來,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皆為非禮。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宜矣。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蓋以為之而莫之應故也。然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息之小者。聖人知其然,謂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故德無不容厚於仁,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故道無不理而薄於義。至於禮,則去而不留,過而不守,止於履之而不處也。是以足進之履猶之禮者,以其卑而可履人之所履,以為禮而踐焉者也。《易》以上天下澤為履,而曰履不處也者,以是故爾。古之至人不知禮之所將,而相忘於道術者,以此。故上仁同於德而無為,上義有以為而立我,上禮則有莫之應者,而未免夫累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徽宗註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玫,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七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眾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疏義曰:道常無為,則無方也,無方則非彼矣,故不可致。然道者德之欽,故失道而後德。德以得之,則在我也,在我則無外矣,故不可致。然德無不容為仁,故失德而後仁。德則無為,七則有愛利之心焉,故仁可為。然為則近乎義,故失德而後仁。仁在所厚義則必欲設於適焉,故義可虧。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自失道以至於禮,每降愈下,去道滋遠,而所失滋眾矣,則以有為則偽,無為則真,故其不同如此。然則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德之所以為上者,有在是爾。且消息不停,王廢更代,物不並盛,陰陽是也。陽用事則陰且退聽,陰用事則陽且伏藏,虧於此者必盈於彼,理相予奪,威德是也。以德為治,威非所先,以威臨下,德在所後,自然之勢,不可易者也。然則父子之禮,貌薄而實厚宜矣。莊子所謂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正此意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鈴衰,則猶木之未盛而其本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又烏能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哉?夫禮之所以相偽如此,不得不去彼取此而滅之也。《記》以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亦貴其有本爾。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徽宗註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億度,玆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疏義曰:仁義禮智,無非德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智雖分於道,亦本於道矣。然則所惡於智者,為其不能行其所無事,以智為鑿故也。矧夫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敝精神於蹇淺而妄億度,以為前識者乎,謂為道之華而非道之實,詛不信然。蓋小識則傷於德,迷識則害於道,若夫前識,則矜聰明而務智巧,方且徇末忘本,不知豐智源而嗇出,雖未至於傷德害道,亦非道之實也。若然則作偽,心勞日拙而智有所困矣,玆識也祗,所以為愚之始歟?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者以此。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疏義曰:以禮相偽,以智為鑿,皆遠於道而在彼者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皆離道未遠而在此者也。在彼者徇末而忘本,故道之所去。在此者歸厚而敦薄,務實而去華,故道之所尚。道之所尚,厚而不薄,實而無華,惟見善明,用心剛。智足以自知,性修反德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者,為能去彼有為之偽,取此無為之真也,《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若所謂敦仁,言於仁為至厚。若所謂敦化,言於化為至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人生而厚,天之性也。誠能復其性之至厚,則動必迪吉,孰有悔吝之虞哉。此復之本於此,以言敦復無悔也。非智足以自知,不能與此,故其象言中以自考,而孔子以謂復以自知也,大丈夫所以備道全德,蓋本於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險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疏義曰:道冥於無,則藏於有一之未形;道降於有,則判於有萬之不同。渾淪之中,自無出有,兩儀以此奠位,萬物以此散殊,幽焉而神,明焉而人,皆會於一。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凡麗於域中,攝於有數者,孰不本於是一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必虛其一。九疇以五行為初,而五行必一,曰水是一者,肇於有數之始,即一可以行萬,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也。莊子謂通於一,萬事畢,豈非德總乎道之所一,能得其一而同焉,推而行之,其用為無窮耶?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固自全,非由外鑠。一流於偽,則真精俄喪,與接為構,曰以心闕矣。必欲全汝形而無搖汝精,果何道而致之乎?實在於致一以專之,抱一以保之,守一以固之,然後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與神合,而不離矣。《易》曰言致一也,致一則用志不分矣,故不二。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抱一則善抱不脫矣,故不離。莊子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一則靜專而不流矣,故不遷。知此三者斯可以得一,然得之非艱,知其一之為艱。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所謂少則得是也。不能知一則而偶之者,皆不離於一而已,是以乾道若難,確然在上而常易,易則純粹而不雜,《易》於《乾》言剛健中正純粹精,非天得一以清然乎?坤道若繁,險然而常簡,簡則靜止而不變,《易》於《坤》言至靜而德方,非地得一以寧然乎?難測難識,至幽而無形者,神也。神雖至幽,而禍福緣類為甚顯,以得一則不昧也。不將不迎,至虛而善應者,谷也。谷以至虛,而洪纖響答為無差,以得一則無窮也。天地襲精而為陰陽,陰陽專精而為四時,四時散精而為萬物,萬物以精化形者,在此而已,故得一以生。惟虛可以應實,惟靜可以攝動,惟一可以行萬,侯王以獨制眾者,體此而已,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侯王,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辨為三極,雖有各立之體,達為三才,乃有相通之用。原其所以清,所以寧,所以為天下正者,豈離於一哉?是一也,根於固有,合於自然,至靜之中,其精甚真。由一以致之而已,非他求而外鑠也,所謂其致之一,亶其然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 徽宗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 疏義曰:施而運之者,天也。其體純粹,所以職生覆。收而積之者,地也。其性靜翕,所以職形載。裂則非純粹也,將何以覆?發則非靜翕也,將何以載?神依人而行,示而常寂,歇則無所示,非所謂靈矣。谷受而不藏,應而曲當,竭則莫之應,非所謂盈矣。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精氣為物,言其東也,聚則得一以生,物於此乎始。遊魂為變,言其散也,散則失一以滅,物於此終。惟以正御變,常得其一,然後能正眾生,超然獨立乎萬物之上而長處顯矣。求其貴高而不危,在此而已。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徽宗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疏義曰:貴賤有常勢,高下有定位,茲不易之分也。然貴必以賤為本,以貴之所恃以為固者,賤而已,若所謂致邦本之固,必取於民之微賤者是也。高必以下為基,以高之所自起者,下而已,若所謂立太平之基,必取於臺萊之卑小者是也。蓋治玉所資者石,丘山所積者卑,稽諸物理,莫不皆然,況於人事乎?世之人逐於末流,而不知去道愈遠,故所睹者末。聖人則探其本,能體道之虛,而無亢滿之累也。膠於陳迹,而不知燭理所在,故所見者成。聖人則察其微,能灼見厥理,而無夸耀之述也,是宜常得一,雖歷萬變而無弊歟?《詩》歌天保,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亦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而已,此基本所以固於無窮也。考其作詩之終,乃見聖人以道御時,使盈不至於極而虧,升不至於極而條,成而不壞,盛而不衰,以保天下之治者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徽宗註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責高而不蹶,其以此乎? 疏義曰:侯王以獨制眾,則其總攝亦云普矣,以德撫世,則其經濟固盡善矣。宜其名有殊稱,方且以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為稱,盡其謙沖退託,不以勢自居故也,非知本者能若是乎?苟卿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是皆聖人謙虛之道,惟侯王知以此自牧,所以能長守貴高於萬斯年而弗失也,非以賤為本邪,非乎? 故致數譽無譽。 徽宗註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政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疏義曰:不以人之卑而自高,然後人樂推之;不以人之賤而自貴,然後人尊榮之。自高以勝物,刻意而高也,何取於高?自貴以賤物,挾勢而貴也,何取於貴?柔之勝剛,理之常也,剛而不知守以柔,是知伸而不知屈;光而不耀,道之復也,白而不知守以黑,是知彰而不知微。以此夸末世之弊,雖足以賣名聲而致數譽,是特違道以干之爾。若然,則不虞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又安能逃孟子之所譏哉?求譽若此,則名浮於實果何異。溝洽之盈,其涸可立而待,譽未幾而毀隨之,何可長也。謂之無譽,不亦宜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徽宗註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疏義曰:德有體用,常變寓焉。妙觀其體,則斂萬可以歸一;泛觀其用,則以一可以行萬。調而應之,無施不可,往來乎出入之機,周流於變通之用,所以為真一者,湛然而獨存,豈若碌碌之玉貴而不能賤,落落之石賤而不能貴,拘於一定之體,執而不變者哉?聖人其動若水,善時而無所失,避礙而無不通,方圓曲直,應變無常,又何底滯之有?測之益深,窮之益遠,雖涉萬變,而常可以為乎未始離於一信,所謂真得一者也。所以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以一無貴賤故也。老氏既明一義,又慮執方之士蔽於一曲,不該不徧而昧於至理,堅如玉石,泥而不通,故申言之。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正此意爾。故不欲綠綠如玉,落落如石,惟大而化之之聖為能及此。《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聖人之所以知化,亦無為無不為而已,是謂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徽宗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歛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束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于莫為,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疏義曰:動因靜立,凡天下之動爻復於靜;強因弱成,凡天下之強必積於弱。則動靜相因,強弱相濟,理蓋如此。物之生也,芸然流形,若驟若馳,於其終也,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自然之理也。故方其已往,趨乎動出之塗,及其反本,則復乎至靜之域,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動無非我,則反者所以立動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柔者道之剛,故柔勝剛。弱者道之強,故弱勝強。柔弱者,道之無也。無之以為用,故道之用用乃在乎此。然而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所不勝,而得常勝之道。莊子所謂積眾小不勝為大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正謂此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易》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即四時以觀之,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故必歛藏於冬而後蕃鮮於春。即水之性以觀之,納汙受垢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何以異此?今夫萬物以形相生,而形形者不形形之所形已。墮於有,則形形者,所謂無也。無不廢有,故申於東南而有;物不終有,故屈於西北而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則以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極必歸於無也,如東西,其方雖異,廢一不可。彼溺於道之靜,若季真之莫為,蔽於道之動,若接子之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徽宗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疏義曰:工具,人器而已,故上下皆弗違。士則其才上達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其才上達則志於道可知。所謂上士,即善為士而能尚志者也,故其於聞道,用心專信之篤,日知其所亡,力行而弗怠,始乎為士,終乎為聖,苟卿所謂真積力久者是也。居之安,守之固,學如不及,沒而後止,未嘗願息而中晝,《記》 所謂至誠不息者是也。若顏子語之而不惰,其勤而行之之謂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徽宗註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疏義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士則非上智矣,故於聞道,或用心不剛焉。蓋於道見疑,是以有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中士不可以語上,以用心不剛而有疑心故也。心疑則有礙,所以一入焉若存,一出焉若亡。用志分而不能致一也,若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其若存若亡之謂歟?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徽宗註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 疏義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下士無高遠之見而同乎流俗,所存者未定,信不足以有守,所見者不廣,智不足以與明,故以道為羞稱而笑之也。蓋以彼笑此,有分守焉。彼之所見累於物而非道,此之所聞一於道而非物,蓋道非形色聲味之可傳,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蓋遠矣。道之與物不侔如此,以有分守故也,是以不無淺識之所笑也。使道如物之累於迹,可以投眾人之所好,道亦小矣,故不笑不足以為道。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蓋聲至於妙則知音者寡,言至於妙則知言者寡。道至妙,猶大聲之與高言也,故其為士者笑之。經所謂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義與此同。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徽宗註曰:若曰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疏義曰:《易》曰:曰月相推而明生。苟卿曰:在天者,莫明於曰月。夫曰昱乎晝,月昱乎夜,曰月麗中天而冒下土,可謂明也。道之炳而易見,示而不祕,若曰月之光照臨下土,是為明道。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智謀不用,豐智源而音出,惛然若亡而存,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徽宗註曰:同歸而殊塗,一政而百慮。 疏義曰:夷之為言易也,易則不險。夷之為言常也,常則無變。夫不險而無變,則道一而已,經所謂大道甚夷是已。道雖一也,然天下之群實由此以出,天下之群動由此以立,若不一而其實一也。蓋絲合而純,則為無類,類則離而不一矣。道之致用,雖裂為多岐,而其歸則同,雖散為萬態,而其致則一,《繫辭》 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政也。 進道若退, 徽宗註曰:顏淵以退為進,莊子以謂坐忘。 疏義曰:為學所以窮理,故日益。為道所以盡性,故日損。為學日益,則以進為退也。為道日損,則以退為進也。仲尼之稱顏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則顏子嘗進於道矣。然而始則忘仁義,中則忘禮樂,終至於坐忘,自述觀之,疑若退也,然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其為退乃所以為進也。故楊雄以謂昔者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而莊子稱其坐忘也。 上德若谷, 徽宗註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疏義曰:莊子曰:德兼於道。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蓋道不在有,亦不在無,非有非無,惟虛而已,德猶是也。故如谷之虛而能應,應而不竭,《書》所謂若德裕乃身是已。如谷之虛而能受,受而不藏,莊子所謂德無不容是已。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其是之謂歟? 大白若辱, 徽宗註曰:滌除玄覽,不睹一疵,大白也。處眾人之所惡,故若辱。 疏義曰:經曰明白洞達,莊子曰以此白心,則大白者,道之入於無疵者也。自非滌除外慕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烏能不睹一疵乎?夫惟能無疵,則異俗而不同乎俗,畸人而不群於人,猶之水也,處眾人所惡,故若辱。莊子載老氏之道術有曰知其白,守其辱,蓋見於此。 廣德若不足, 徽宗註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疏義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夫德至於無不容,可謂廣矣,然自以為有餘,則不廣也。惟不自以為有餘,則廣廣乎其無不容矣。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之謂也。顏氏之子德冠四科,德則廣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非若不足而何?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河伯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曾不知東海之大,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徽宗註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疏義曰:聖人之應世,無心而已。惟無心,故於興事造業,皆緣於不得已,莊子所謂不得已於事也。然帝王無為而天下功,雖躊躇以興事,不期於功之成,而每成功焉,則其建德以有為,疑若偷焉,以其無心故也。 《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則苟且而近乎薄,以其無心,故若偷。 質真若渝, 徽宗註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疏義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渝之為言變也。真人之用心,絕仁本而弗殖,豐智源而嗇出,於見則無愛,於聽則無淫,於氣則充實而無餒,自得其得而不假人為,雖辨於物而以真冥妄,雖攖而寧,所謂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即染而淨,所謂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故若渝。 大方無隅, 徽宗註曰: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疏義曰: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陰陽不測,神所以無方之可求,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道所以有方之可指。道雖有方可指,然與物宛轉,無介辨之迹,偶而應之,無刻制之行,是為無方之方也,蓋異乎德之有隅矣,故方而不割。《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德有隅可知。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則道無隅可知。 大器晚成, 徽宗註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疏義曰:有形則有名,有分則有守,此器也。然有出器入覺,造形而上,立於不測,不可為量數,行於無有,獨超乎象先者,此不器之器也。不器之器者,道也。道不可以頓進而語,道非其序者,安取道?故晚成焉。陽積成暑,陰積成寒,非一日也,豈益生以為祥,揠苗而助長乎? 大音希聲, 徽宗註曰:動于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疏義曰:聲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所謂聲聲即大音也。雖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故謂之希。蓋希則概而有問,非聽所聞故也,莊子所謂動於無方是也。雖聽之不聞,然而清濁高下,叱吸叫譹,感之斯應,而五聲不得不嗚其為,音也,蓋亦大矣。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淮南子》曰:無聲而有五音嗚焉。其大音希聲之謂歟? 大象無形, 徽宗註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疏義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所謂形形即大象也。雖使離朱當晝拭訾以揚眉而望之,不見其形,故謂之大象。蓋見乃謂之象,既已有見矣,而曰無形,則不形之形也,莊子所謂居於窈冥是也。雖無形之可見,然天下之有形者,皆生於此,其為象也亦大矣。經曰:無物之象。《淮南子》曰:無形而有形生焉。其大象無形之謂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徽宗註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其餘事猶足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疏義曰:道無在無乎不在,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物,而不離於有名有物者也。是以自明道至于大象,其名不同,要之皆道也。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未離有名而不可以智索;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雖未離有物而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雖曰強名,而道之本原欲名之不可得也,則以道隱無名故也。聖人得乎道,以至無妙天下之有,以至虛運天下之實,故既以與人己愈有,予而不費,既以與人己愈多,應而不匱,為萬物之所係,為一化之所待,善救人而無棄人,善救物而無棄物。物來有感,吾則與物委蛇,而未始或遺;物逝而往,吾則與物俱休,而未始為累。在彼者以自取而受,而終必還其宗,在此者以不與而濟,而本實無所費,莫不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夫天下之理,徂者且往爾,要之將自復,殂者且死爾,要之將自生。道之貸物,終則有始,莫或已也,故謂之且焉。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亦在乎勤而行之爾。誠能真積力久,則造乎不形而與道為一,止乎無所化而亙古今常存,緒餘以治國家,土直以治天下,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功,在我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篇始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而終以道善貸且成,則以下學而上達,善為士者舉皆然也,苟卿亦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此之謂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九 太學生江激疏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徽宗註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疏義曰: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謂之太初,則以雜乎芒芴之間,神化為氣之時也,當是時,未始有物,窅然空然,惟無而已,則太初之先一無所有者,有無故也。莊子所謂有無也者,是已謂之者無,蓋無有矣。既曰無有,斯無名矣。且天無立物之名,物有生而名自著,物成數定,然後多寡可名焉。方其無有,則未始有物,未始有物,則非貌像聲色之可求也,孰得而名之?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又曰道常無名。然則無名有無者,道之體也,道之體本無也,而無不廢有,是以無動.不生無而生有,象玆所兆,自無適有,數始立焉,則一之所起,本於太初而已,此道降而出者爾。若夫道冥於無,則復於渾淪,氣且未見,一亦不可得矣,所謂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列子所謂易變而為一是也。 一生二, 徽宗註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疏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以有天有地,然後上下有差故爾。乾,天也,其數奇。坤,地也,其數耦。故易稱天一地二,有天然後有地,則天一而地二次之也。水淵而虛,因實以成體,辨而後有,察於卦為坎,坎藏一也,故一曰水。火動而速,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於卦為離,離圍二焉,故二曰火。自道而降,水幾於道,然水中有火,相繼以成,則水一而火二次之也。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則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為身之本,精全則神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矣。是以不離精謂之神人,則精具而神從之也。 二生三, 徽宗註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疏義曰: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一者奇也,獨奇不生。二者耦也,獨耦不成。一奇一耦,而三且生矣。推本言之,道之大原,其獨無對,萬物雖多,與我為一。既謂之一,不得無言,則一者一物,而言之者又一物也,是一與言為二矣。一為奇,二為耦,奇耦相生,有二則有三也,是二與一為三矣。夫自無適有,以至於三,婁以聚之至於無窮,蓋數之自然而不可易者也。 三生萬物。 徽宗註曰:天筆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曆不能計。 疏義曰:渾淪既判,輕清上積得乎陽,而其數奇,故天兆一於北。重濁下凝得乎陰,而其數耦,故地耦二於南。然天統元氣,地統元形,必有統元識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必有職教化者,是則天地設位而人成位乎其中矣。三才既具,則本乎天者親上屬,天清而散,本乎地者親下屬,地濁而聚,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林林以生,職職以殖,而萬象分矣。舉天下萬物之多,莫不因於此,故《易》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以其多者號而讀之也,彼其芸芸紛錯,可勝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微宗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曰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疏義曰: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陽以動吐,陰以靜翕,故陰止而靜。陽以熙之,陰以凝之,故陽融而亨。惟止而靜,故萬物之生,其後之所負者,皆陰而背北。惟融而亨,故萬物之生,其前之所抱者,皆陽而胸南。以萬物負陰,故君子順陰之義,所以日入而息,以夜道極陰也,《易》 所謂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是已。以萬物抱陽,故聖人所以嚮明而治,以晝道極陽也,《語》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是也。非陰陽無以成沖氣,沖氣則天一為之本,天五為之中也。非沖氣無以成至和,和則不偏於陽,不毗於陰,陰陽之中也。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蓋陽明陰晦,赫赫則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 原也;陽生陰殺,肅肅則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肅肅出乎天而天氣下降,赫赫發乎地而地氣上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楊雄亦曰:天地交而萬物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徽宗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己極而返,己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疏義曰:升極而降,故高者下之。盛極而衰,故饒者取之。妙而為陰陽,散而為事物,莫不皆然,則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聖人探本知微,是以時消而消,時息而息,彼為盈虛,與之為盈虛,保合大和,與時偕行而不失,故雖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為稱而不恥也。彼天下之勢,極者雖必虧,此則守其成而不虧,知己極而返也;滿者雖又溢,此則持其盈而不溢,知己滿而損也。所以長守富貴,居上而不危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徽宗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疏義曰:凡木之生,以敷榮蕃鮮為益,以凋瘁搖落為損,木落則有所損,然且糞其本焉,是乃所以為益也。《易》言損而不已必益,所謂損之而益也。月昱乎晝,至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方其盈也,可謂益矣,然過滿而食,損之者至矣。《易》言益而不已鈴次,所謂益之而損也。然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是以孤寡不穀,王公以為稱,雖若自損,乃所以政益而處貴高之道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徽宗註曰: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粱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疏義曰:自事言之,弱固不可敵強,柔亦不能先剛,則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自道言之,堅強居下,柔弱處上,柔弱固可以勝剛強也。若然,則我之所教固異乎人矣。我之所教雖異於人,而人之所教亦我之義,特以人之所教在事,我之所教在道,其於以強弱為教,則一也。蓋堅強者死之徒,而強梁則有我而好爭,故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以為教父,不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徽宗註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彊。惟夫常勝之道在柔,此古之博大真人必以懦弱謙下為表也。以濡弱謙下為表,則以深為根,無事於堅,以堅則毀故也,以約為紀,無事於銳,以說則挫故也。無事乎堅與說,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從其強梁,隨其曲傳,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虛靜之中未始或件,所謂天下之至柔,其在是也。及其幹旋萬有,宰制群動,應之於無窮,資焉而不匱,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是又馳騁天下之至堅,無往而不勝者也。莊周論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可謂深明乎此。觀風之行乎太虛,指我則勝我,增我亦勝我,至其披拂鼓舞,物無不聽其命。水之處乎柔弱,次之東則東流,次之西則西流,至其攻堅強者,物莫之能先,是亦積小不勝之意也,孰謂天下之至柔不能馳騁天下之至堅乎? 無有入於無間, 徽宗註曰:《 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游無朕者,其執能之? 疏義曰:物墮於形氣者,每為形氣之所拘,以己所易憐,彼所難殊,不知大化密移,默運於冥冥之中,無為而常自然,役於造物之巧,無得而贅虧。《莊子·外篇》所以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月憐心,是皆有所拘而然也。蓋足之行域於遠近,力有所不至;目之視倪於細大,明有所不及。惟神則幽無形而深不測,其運無乎不在,速不疾而至不行,其用無乎不妙,適無方之傳,而未始滯於形體者也。神之無方,至虛而已,以至虛而利用出入,宜其無適而不可者也,果非以無有入於無間之謂乎?《內篇》論養生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蓋萬物以形相生,而神為之主,庖以調和為事,所以養人。地二生火,在人為神。丁,火之陰,神之相也。以神為用,故若庖丁之解牛。至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歌行,則一心自照,天理皆得,批大卻,導大竅,而毫芒不判,恢恢乎其於遊刃鈴有餘地,莫不釋然四解矣。雖然解牛之喻以無厚入有間,猶能迎刃而解,,況以無有入於無間,則六通四闢,明白洞達,了無纖翳之滯礙矣,自非天下之至虛、體盡無窮而道無朕者疇克爾。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玆所以為有益。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道之真體寂然不動是也。無不為者,道之妙用感而遂通是也。惟其無為而無不為,故以天下之至柔而勝剛,以天下之至無而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柔之勝剛,所謂積於柔者必剛也。無之攝有,所謂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也。其妙用如此,又豈樂從事於務哉?運量酬醉,時出而應之,萬變雖雜,而所以無為者,固自若也。無為則事奚足棄?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則其有益孰大於是?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徽宗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疏義曰:言有當愆,孰若不言之教?妙通心術而設之以神,《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 此也。為有成虧,孰若無為之益?得於自然而不虧其真,莊子所謂無益損乎其真者,此也。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知不言之教固神矣。天地以無為而清寧,則知無為之益固真矣。聖人以天地為宗,故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樸者,道之全體,惟道能總攝群有,所謂守小樸而物自賓也。無為者,道之自然,惟道能幹旋化樞,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然則不言之教,無為之益,非體無盡道者不能知此。聖人者道之極,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徽宗註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疏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徇,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坏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疏義曰:務內觀者取足於身,誠其身者真樂內融,則一身之中,眾美咸具,何往而不自適。世之昧者,不能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乃矜攪外務,見得忘形,汲汲於名,以危其身,殊不知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名與身孰親?孳孳為利,以害其生,殊不知生固重於隋侯之珠,利固輕於千仞之雀,身與貨孰多?惟不介意於儻來而以守身為本,然後能自適其性分,以道為重矣。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未聞其干於名。顏回樂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未聞其累於貨。所重者,道而已。是以至願名譽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不急於人知,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則萬物皆備,貨非所多也。於此而不能明親疏多寡之辨,其為智亦疏矣。故有見生於可欲,乃殘生傷性,以身為徇而忘其真,如伯夷見名之可欲,餓于首陽之下是也,盜跖見利之可欲,暴于束陵之上是也,此皆昧於至理,惑而不能解也。惟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非生之所待而生也,此有道者所以能保身全生而異於世俗者歟? 得與亡孰病? 徽宗註曰:烈士徇名,食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贊之軀,病孰甚焉? 疏義曰:求諸性分之內者,有益於得;求諸性分之外者,無益於得。有益於得,則其得也裕然而有餘;無益於得,則其得也歉然常不足。夫惟不足,故烈士徇名,則累於名高而不知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黃夫徇利,則累於利厚而不知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蓋萬物之理相為消長,有得則亡或繼之,故諸所病。然其得之也,是豈真得之哉?名與貨皆儻來之寄耳,寄之其來不可圖,其去不可止。而其亡也,乃至於損德塞性,苦身疾作,喪無名之樸而失其至真,忘不貲之軀而捨其至貴,則其病大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徽宗註曰:無慕於外,則嗇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疏義曰:重內而不重外,然後能無慕於外;見性而不見物,然後能無累於物。不生外慕,則無多欲之逐,故嗇而不費,非至於甚愛必大費者也。不為物累,則無食積之憂,故守而不失,非至於多藏必厚亡者也。雖然利之在天下,民咸用之,無所不通,有取斯有予,其出入常相權,有積斯有散,其盈虛常相代,乃必至之理。勢若循環之不能自已,又烏可恃為長久而認為己有哉?雖執之使留,且自冥冥中去矣,惜夫世俗莫之悟。經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知足不辱, 徽宗註曰: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疏義曰:一性之真,萬善充足,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不假勢物而無所歉,則亦處乎不淫之度而已。蓋不淫之度者,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以此安其性命之情,則真君高世,良貴在我J 所以為義榮者,物無以尚之,又何辱之有哉? 知止不殆, 徽宗註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 疏義曰:域於流動之機者,一息不停。固有默使之者,若有機緘而不得已,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雖行之於無止,而不知有真止者。存勢物之徒,不能徐觀一性,鎰淵靜不遷之宗,乃與物為偶,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且將菁然痕役而不知其所歸,豈不危其身耶?真人則不然,超然獨立乎形器之上,與造物者進,與無終始者為友,蓋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虛靜之中默與道會,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入而莫之能傷,又何危殆之患哉?老氏於道常無名亦曰知止所以不殆,蓋非通乎物之所造者,不能與此。 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疏義曰:即理以觀物,則無常之分,有積有做。即妙以觀性,則真常湛專,無古無今。以性逐物則性與物俱馳,以性辨物則物無自而入。世之人昧於至理,馳其形性,港之萬物,以易所固有,於是好名者困於志,徇利者忘其真,至於名辱而罔覺,身危而莫顧,交戰於利害之域,何可長也。聖人盡性而足,故能貴愛其身,不以害其生,三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為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徽宗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洛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疏義曰:道未始有封,彊為之名曰大。既謂之大,則未離方體,寓於域中,而居四大之一焉。蓋道覆載萬物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人位乎兩問,體道之全以配天地,故皆名於大。則其由是道以出應天下,天造地設,發越顯著,以彰制作之妙,其成也可謂大矣。然而道無成虧,烏至而倪小大?世之人徒知聖人以道之緒餘土直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豐功茂烈,巍乎其成,而不知道之妙用,本於精神心術之微。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惟其無成與虧,所以謂之大成。夫萬物之理,成極而壞,功成者環,名成者虧,能不有其成,然後成矣而不壞。是以神人無功,非無功也,功成不居;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名成不恃。故能去功與名,還與眾人,所以謂之若缺。大成若缺,非特不自有其成而已,又見其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神無方,無方則化而栽之以盡其變,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又豈膠於故常,而不能利用出入者哉?宜乎其用不弊也。孔子集清和任之大成,所以為聖之時,得此故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三聖之制行,玉振之謂也。執一不變,能成其終而已。至於金聲而玉振,則知化合變,所以能成始而成終也,故曰大哉孔子。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徽宗註曰: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疏義曰:道之真體,包裹六極,廓然而無所不存。道之妙用,周流六虛,廣乎其無所不被。聖人得道之渾全以出應天下,充塞無外,覆禱萬物而莫見其吵,贍足萬有,鼓舞群眾,而求者與之,則其用之所以妙有,不可得而知,其為盈也,豈不優優大哉。然而酬醉之用常本於淵靜之宗,盈而不能虛,則無以應物。惟以道之虛應彼群實,然後能沖而用之淵泉而時出之矣。是以注焉不滿,資焉不匱,施之不竭,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其用不窮,故謂之大盈若沖。雖然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故保此道者不欲盈。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宜老子以是言告孔子也。夫有若無,實若虛,學者之能事,良賈之深藏,亦若是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聖人之虛己、君子之容貌在是焉。即此以觀,則大盈若沖可以類推矣。 大直若屈, 徽宗註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 疏義曰:聖人虛己以遊世,汎應曲當,無往而不直者,以順物之變故也。是以委蛇而不傷其全,曲折而不失其正,從其強粱,隨其曲轉,未嘗崖異以自處焉。是雖委蛇曲折,與之宛轉,所以為大直者,有不可得而控者矣。謂之不求其肆者,此也,豈非若屈之意歟?莊子於《人間世》言:內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蓋人間世者,出而應乎人也。內既徒於人,不可以徑庭,宜其外曲焉,則大直若屈可知矣。 大巧若拙, 徽宗註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睹其妙,故若拙。 疏義曰:聖人至無,以供其求,善貸且成而其巧妙者,亦猶造化賦物之形者也。是以圓方而不離於規矩,曲直而不違其繩墨,形體自著,藻色自彰,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焉。是雖方圓曲直,各盡其妙,所以為大巧者,有不可得而測識者矣。謂之莫睹其妙者此也,豈非若拙之謂歟?莊子於《大宗師》 言:履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蓋大宗師者,萬物之所宗也。萬物既宗,則生而不有,宜其不為巧,則大巧若拙可知矣。 大辯若訥。 徽宗註曰:不言之辮,是謂大辮,惠施多方,其辦小矣。 疏義曰:至言去言,得於忘言,然後為言之至。所責千不言之辮者,其至言去言之謂歟?莊子曰:大辮不一唁言。夫惟不言,是謂大辮。聖人不以善辦為能,深造默識,至理所存,不官而喻,無俟於容聲,故若餉。彼惠施之多方,特辨者之囿也,支離曼衍而不得其要,曾何足以語極,飲其道舛而一不合,駁而不純,自謂辮且博,不幾於一蚊一蝱之勞,則其辮亦以小矣,孰知不官之辦?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徽宗註曰:陽動而躁,枚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 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疏義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受天地之中,稟沖和之氣。一動而躁,則發於陽,而其熱焦火,故勝寒。一止而靜,則息於陰,而其寒凝冰,故勝熱。二者既有陰陽之患,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不適厭中,非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若然則方且為物汨,淪胥於波蕩之域,方且與動爭,交戰於利害之塗,陰陽為之寇,宜其不能正天下也。惟無勝寒之躁,使之陽而不散,無勝熱之靜,使之陰而不密,然後能清靜為天下正。蓋不雜而清,斯為請之至,若所謂嘐乎其清者是也。抱神以靜,斯為靜之至,若所謂寂然不動者是也。必靜必清,則表正而影必端,天下不期正而官正矣。老氏於道常無為亦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謂之無為,則澹然而已。求其勝寒之躁,勝熱之靜,蓋無有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徽宗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疏義曰:在天下以道,故天下不淫其性;宥天下以道,故天下不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耕而食,識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各樂其業,而無夸跋外慕之爭矣。方且力本務農,服勤南畝,糞其田疇而已,雖有追風逐電之驥足,亦將卻之而不用也,惟天下有道能知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徽宗註曰:強凌弱,眾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疏義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義以分則和,和則一。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強者恃力,或至於凌弱。眾則恃勢,或至於暴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戎馬生於郊,而疆界不能正,蓋不知以道治天下故也。 罪莫大於可欲, 徽宗註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次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疏義曰:心本湛然,欲慮不萌,物誘於外,情斯有欲。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以志師氣,交物而忘返,則氣為之餒,而心始亂矣。故不見可欲,則使心不亂,蔽蒙之民,昧此而罔覺。累於名高者,則見名之可欲,累於厚利者,則見利之可欲,得失交戰於胸中,至於次性命之情以爭之,貪汙誣偽,無不為己,罪之所以起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徽宗註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疏義曰:陽明以晉富而為福,陰晦以退耗而為禍,是以福主衍而禍則武。然福與禍鄰,而禍福相倚伏,故平為福,而有餘為禍焉。《傳》所謂福莫長於無禍者,以此。苟不知足而務食得,則高明之家固有鬼瞰其室者,禍孰大於是?惟處乎不淫之度,則知足不辱矣,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徽宗註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疏義曰:如谷虛而受,受而不積;如谷虛而應,應而不著。有道者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而已。苟為以物易己,見得而忘形,不能以公義勝私欲,人之所違也,咎孰大於是?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徽宗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甚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曰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疏義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內觀一己,無物不備。至足之分,非外鑠也,惟知至足之在我,而不志乎期費,則有萬不同,其應不匱,豈不常足乎?惟其人見可欲,則貴貨而不知足,不知足則矜攬外慕而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至於戎馬生於郊矣。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則機心不生而純白備,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徽宗註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放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玆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疏義曰:生齒至眾,機務至繁,天下之大,宜難知也。然揆理則天下雖大,無所遁其情,所謂知之以智者,揆以理故也。窈然無際,漢然無分,天道之遠,宜難見也。然視於無形,則天道雖遠,與之同其妙,所謂見之以心者,視於無形故也。蓋道降而出,出而生智,玄升而入,入而生神,智者通於神者也。神之無方,利用出入,無遠弗屆,智與乎神,所以能周乎萬物,雖遠在八荒之外而無不察,又何待於出戶而知天下哉?莊子曰大智觀於遠,近智周萬物者,以此。道心惟微,搏之不得,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則心者會於道者也。道之大本先天地生,運而無積,心虛集道,所以能潛神明,雖藏於不形而無不燭,又何待於窺牖而見天道哉?揚雄曰天地神明而不測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心潛神明者,以此。雖然無遠不察,則智亦大矣;無幽不燭,則心亦神矣。智無不知,心無不見,兩者同出於虛靜之宗,廓然洞達,則千變萬化,未始有窮,六通四闢,無乎不在。即其妙用始此,蓋有所謂立本厚者存,莊周論人心而言其疾晚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以是故爾。蓋晚仰之間則其速如馳,四海之外則其遠無疆,於如馳之疾,撫無疆之域,而至于再,非兆於變化,其孰能之哉?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歟?,列子所謂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同意。密運則化之妙,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獨化之本,若運轉而不能自已。由是觀之,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豈徒得之於智慮心術之微而已哉?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徽宗註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疏義曰:《易》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情,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大壯者,大而交於物。復者,小而辨於物。惟其與物辨,故方其並作,而趨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大不可以俄而測度也,能以心腹心,使心合於無,則天地之心即吾之心矣。所以有貴於復者,在於靜止而不在於動出也。即此以觀,則道在邇而不必求之遠,近取諸身可矣。一身之中萬物咸備,內觀者無不取足,天下之至蹟盡在是矣。能致虛守靜而會之以心,則道將為汝居,又何俟於遠求耶?求之陰陽,則道雖不離陰陽,而非陰陽之所能盡;求之於度數,則道雖富於度數,而非度數之所能窮。或五年而未得,或十有二年而未得,所以去道彌遠,而所知彌少也。夫道若大路然,炳而易見,豈難知哉?病不求之耳。能反求諸己,則無形而心成,將進乎博之不必知者矣,又何患於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徽宗註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五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疏義曰:行而知之,則足之所至者近,不能察其遠;見而名之,則目之所逮者淺,不能燭其幽。惟以吾之智知天下,然後超然遠識,足以通天下之理,雖不出戶而知之矣,是謂不行而知。惟以吾之心見天道,然後洞然玄覽,足以探天道之妙,雖不窺牖而見之矣,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則天下之大,天道之遠,未嘗有心於其間,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夫何為哉?處無為之事,而天下將自功,所以斡妙用而獨得於昭曠之先,固自有其道。世莫得而知之,殆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莊子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詛非不為而成之意耶?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徽宗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疏義曰:道不可致,然有所謂可致者,唯學而已。蓋學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自可欲之善,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仁之於父子,修之至於聖人之天道,此《語》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苟子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也。惟知務學,則日有所就而知其所亡,月有所將而無忘其所能,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而道將為汝居,可謂汨加益而道積于厥躬矣。顏氏之子知堅高之可慕,忘鑽仰之為勞,問仁則請事,斯語得善則拳拳服膺而沸失,孔子謂之日吾見其進也,不亦宜乎? 為道日損。 徽宗註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連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疏義曰:知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則不累於形而墮支體矣。知吾生有涯而知無涯,則不鑿於智而黜聰明矣。離形而形不能礙,去智而智無所困,不內變,不外從,事則一毫不櫻而萬事銷亡,故日損。莊子曰連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年運而往,至於六十而六十化,可謂忘年而與化為人者也。觀蘧伯玉之使,以謂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則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可知已。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矣。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疏義曰:學欲博,恥一物之不知,所以窮物理而該天下之有,故日益。道貴要,無一毫之攖,所以盡其性而造至妙之無,故日損。蓋一性之真,不睹一疵,惟道以盡性而造無,則不特未始有無,必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所謂又損也,夫然故能應能定,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則寂然不動而能定也,無不為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也。靜而處己,內聖之道以全;動而接物,外王之業以成。一本於此,故莊子言靜而聖,動而王,繼之以無為而尊。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枚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直父所以去那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疏義曰:一囿於物,必有非物者,然後能運之;一墮於器,必有不器者,然後能統之。六合雖大,已囿於物矣,非物者,道也。已墮於器矣,不器者,道也。體道則事無事,故用天下而有餘,莊子所謂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者此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可知已。非道則執於事,故為天下用而不足,經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者此也。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可知已。聖人以道之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成,皆緣於不得已。偶而應之,雖我忘天下而天下將自賓,若太王直父不以養傷生,不以利累形,避狄人之難,去那而成國於岐山之下,蓋得乎此。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九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 太學生江澂疏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徽宗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疏義曰:心虛一而靜,惟虛故能運實,惟靜故能攝動。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聖人極物之真而守其本,是以無所不包,而照知四方。莊子以謂聖人之心,萬物之照,蓋言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無常心故也。猶之鑑焉,不將不迎,妍醜畢見,無所次擇;猶之谷焉,受而能應,巨細皆赴,無所去取,何常之有?雖然《易》以立心勿怛為凶,孟子以無怛產有。怛心者,惟士為能,此言無怛心何耶?蓋道所謂怛以變故常,所謂無常者,非若《易》所謂勿怛也,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則其無常是乃所以為有常也。觀諸天道,其視聽自民,其明畏自民,以無心也。聖人無心,法天而已,故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徽宗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疏義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善否相非也。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誕信相譏也。蓋有善而惡為之惡,則善否不並行,離乎偽必著乎情,則誕信不相伴,事物之常分也。世俗之情,膠於物而不探其理,執於事而不揣其本,方且好好而惡惡,方且排非而提是,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自徇殊面而不知大同,豈德也哉。聖人以真冥妄,萬態一視而無取捨之心,善否信誕,蓋將簡之而不得,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知本無善惡也。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知本無誕信也。真妄同於一真,而真偽兩忘,彼是莫得其偶,而是非一致,則其善也,其信也,皆出於德,異乎世俗之所謂善與信焉,是為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誠信而喜之,非偽也,故聖人不億不信。 聖人之在天下喋喋,為天下渾其心。 徽宗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己,則惵惵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疏義曰:知此而辨焉者,聖人所以處己;覺此而冥焉者,聖人所以待。物。是以責己重以周,而待人輕以約,故方其在天下,則自為之時也,方且與民同患,兢兢以為之戒,業業以致其慎,雖無常心,不敢易也,故雖休勿休,惵惵然不自暇逸。及其為天下,則應物之時也,是以冥美惡於一致,付是非於兩行,齊善否,同信誕,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徽宗註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睹,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疏義曰:天雖高而其監卑,天雖遠而其察邇,以天道無心,因物為心故也。是以未嘗用目,自我民視而無所不視,未嘗用耳,自我民聽而無所不聽,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亦以百姓心為心而已。以百姓心為心,則無所容心而得民之心,故動而有作,如大明東升,有目有趾者,待是以成功焉,百姓有不注其耳目者乎?《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是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視儀而動,聽唱而行,則百姓惟聖人之視聽也。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愛之惟恐其不至,保之惟恐其或傷,鞠我育我,顧我復我,其德厚矣。聖人之於人,不翅於父母,則其矜憐撫奄,若保赤子,不可以已也。聖人之治化覆天下,以此故也。 出生人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徽宗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有無之相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凡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莫不皆然,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自無出有,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從有入無,則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然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死生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紀,則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也。造化之所始,所謂精氣為物也。陰陽之所變,所謂遊魂為變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徽宗註曰:與死生為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夫累。 疏義曰:大道既隱,裂為多岐,悅生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蔽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為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道之靜,止於枯槁而為死之徒。與死生為徒,固已囿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為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為徒者,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囿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徽宗註曰:責么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疏義曰:生非我有,則責生者非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一或責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生亡者矣。生者德之光,則忘生者亦非也。是以能尊生者,不以利累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形不養者矣。蚩蚩之民,大惑大愚,不解不靈,倀倀而往,衝衝而活,食生者矜生大厚而不知遺生,忘生者殘生傷性而不知衛生,摘壇索塗,動之死地,形雖未亡而心且死矣。莊子謂之宵人,楊子謂之夜人者,此也。雖謂之不死奚益?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徽宗註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疏義曰:道之不明,以智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與死生為徒,所謂過之者,而動之死地,所謂不及者也。蓋生之徒溺於或使,不能忘年而喪我,常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蔽於莫為,不能為壽而存形,常趣寂而忘身。二家之議,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是以與民不畏威。動之死地者,同於不能攝生焉。蓋為內刑者,陰陽賊之;為外刑者,金木訊之。惟宵人之離外刑,是以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陷于罪罟亦云多矣,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息,生之為有涯,存生之太厚爾。古之得道者異乎此,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故富貴不以養傷生,異乎食生而背理者;知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故食賤不以利累形,異乎忘生而徇利者。知有所謂未嘗死,未嘗生,故不樂壽而不為生之徒;知吾有不忘者存,故不哀夭而不為死之徒。疏觀洞照,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以偶之者,殆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亙古今而常存矣,是豈生生之厚哉。莊子所謂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蓋得乎此。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過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徽宗註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遝物而不摺,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疏義曰:造乎不形,而知形之不形,所以形全;不搖其精,而能精而又精,所以精復。形全而不虧,精復而不失,則去彼人為之偽,合於自然之天,庸詛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耶?且將與天為一矣。若然則得全於天而其天守全,塗卻守神而其神無卻,潛行不窒,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火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高之所不能危,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故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焉。則其不遇兕虎而禽獸弗能賊,不被甲兵而白刃無所加宜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一晦一明。晝夜相承,負陰抱陽,囿於出入之機者,莫逃乎此。如梟之夜明晝昏,鷂之晝明夜昏,非晝夜之異果梟也,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也。凡謂之物而不明乎道者,莫不皆然。唯至人達萬物之理,而知死生之說,超然通乎物之所造,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參萬歲而一成純,曾何死生之足累歟?謂之無死地,不其然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 道生之, 徽宗註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疏義曰:《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道之體也,故常無為。感而遂通,道之用也,故無不為。萬物之多,職職陳露,原其生出,皆本乎道,所謂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也。莊子民:兩無為相合而萬物化。其幾是歟? 德畜之,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疏義曰:生者,德之光。物之未形,無以見德,及其有生,各得其得焉。即其有生言之,故謂之德,蓋德以得之故也。莊子所謂物得以生謂之德,則德畜之也。 物形之, 徽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疏義曰:陰止而靜,則留者陰也。陽動而吐,則動者陽也。獨陽不生,故不留不足以生物。獨陰不成,故留而不動亦不足以生物。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生理以物成而後具,玆非物形之之謂乎? 勢成之。 徽宗註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疏義曰:一囿於物,形質之所以具也。形質既具,體勢之所以成也。若鶴經之長,若鳧經之短,自然相形;若天之自高,若地之自下,自然相傾。玆非形質具而體勢成乎?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徽宗註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疏義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故萬物首之所以為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成而上者,所以為德,以道對德,則道尊而德貴,惟尊也,故勝物而小之,若莊子言天地雖大,未離其內是也。以德對物,則德為貴而物為賤,惟貴也,故物莫能賤之,莊子言至貴國爵并焉是也。孟子曰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則以趙孟之貴非所謂良貴,在物而非德爾。若夫德,則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不可得而賤也,故為天下貴。《傳》曰: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徽宗註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疏義曰:或作之而動,或止之而止者,物也。或相形以長短,或相傾以高下者,勢也。時運無窮,勢物有盡,一囿於物,烏能無弊?一麗於勢,烏能無傾?惟夫真君高世,萬物莫能卑,良貴在我,不因人而得,非假於物也,故無時而弊,非假於勢也,故無時而傾,此所以無古無今而常自若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徽宗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疏義曰:自道生之至勢成之,別而言之,四者所以不同,合而言之,則皆總乎道。故天地為大,皆有其奧,而道則生天生地;人卒雖眾,皆有其奧,而人則相造乎道,此道所以為萬物之奧也。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之化作也,道則由天之人,與之出而不辭。正得秋而萬寶成,萬物之歛藏也,道則由人之天,與之入而不拒。以至雷以動之而出乎震,艮以止之而成乎艮,坤以藏之而養焉,乾以君之而覆焉,剛柔相摩,生出六子而成變化,八卦相盪,運行日月而為寒暑,品物由是以流形,百昌由是以出入,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孰使之然哉?道實冒之爾。老氏於生畜長育成熟養覆皆歸於道,蓋合而言之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生則兆於動出,為則效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疏義曰: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則反隱而之顯,故有兆於動出之意。《 易》 曰變化云為,為則作之而不止,故有效於變化之意。經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長則以貴得民,故有見於統一之意。此三者,降於道而在德者爾。生者自生,化者自化,無愛利之心,此之謂生而不有其功。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矜伐之行,此之謂為而不恃其能。覆載天地,刻彫眾形,無刻制之巧,此之謂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是謂玄德。以玄者妙而小故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徽宗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疏義曰:先天地生者,道也。道常無名,故無名為天地之始。道降域中,天地為大,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經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曰可以為天下母,則始之與母,皆道之稱也。蓋太初者,氣之始,天下有始,自其氣之始言之也。生生之謂易,以為天下母,自其生生者言之也。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之道,則始母之言亦筌蹄爾。無始則入於不生,有始斯能生生矣。以為天下母者,在於有始而已o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徽宗註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義曰:經曰道生之,則道能母萬物而字之矣。萬物由道以出,則道者其母,而物者其子也。不明於道者,不可以物物;能通於道者,所以兼物物。誠能知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故得其母,能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徽宗註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徼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疏義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故通於一而萬事畢。然則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也,不如其約也。蓋日聞所不聞,聞之多也,而所守在約,日見所不見,見之多也,而所守在卓,經所謂少則得,孟子所謂反說約是已。以是窮物之理,則疏觀坐照而不累於物;以是達道之徹,則雖紛而封而不失其妙。所以能或出或入而用無不利,一往一來而其道不窮。泮涣爾游,優游爾休,而全生盡年之道得矣,宜無危殆之患。雖然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必先知其子,然後可以守其母。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徽宗註曰: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為事? 疏義曰:《兌》之彖曰:兌,說也。故兌以言悅。《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門以言出。莊子言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此物誘於外而心悅於內者也。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耳目鼻。神明出焉者也。惟知夫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有以慎汝內,覆卻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含;有以閉汝外,則寂然不動,而不以通物為樂,不見可欲,物無得而引之。若然則樂天無憂,自得其得,孰能弊弊然以物為事,是之謂終身不動。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徽宗註曰: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疏義曰:兌以言悅,閉其兌則物不得誘,開其兌則妄見可欲。物不得誘,則知慎汝內,閉汝外矣。妄見可欲,則以通物為樂,而物得以引之矣。若然者,相刃以與物敵,相靡以與物化,烏知樂天自得,而不以物為事哉?終身役役如此,將以功求成也,而不見其成功,則迷而不知復,困而不能返,失性甚矣,是之謂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徽宗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則小者道之復於無為也。所謂見小,則見道之妙而已。見道之妙,自知故也。唯能自知,故無不知,經所謂自知者明是已。 守柔曰強, 微宗註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疏義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則柔者,道之本也。所謂守柔,則勝己之私而已。勝己之私,自勝故也。唯能自勝,故無不勝,《經》所謂自勝者強是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徽宗註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曰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疏義曰:明之與光,異名同實,從體起用,則明散而為光,故光者,明之用。攝用歸體,則光復歸其明,故明者,光之體。聖人應世,明出為光,則光被四表,是所謂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也。光復為明,則其明上達,是所謂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也。是則用其光而仁雖嘗顯,復歸其明而用固自藏,故若日月之麗于天,而萬物皆照,所謂日月之明,實未嘗虧也。《易》言神明其德,以此故爾。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徽宗註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疏義曰: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化為神奇,此物化之無常也。若乃復命則不然,去智與故而遺物離人,歸於寂定而復歸于明,亙古今而常存,更萬形而不易,豈與物俱化哉?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全其形生,此所以體常而無患也。則與夫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不異哉?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徽宗註曰: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辮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疏義曰:曰奢曰泰,道之所去,故經曰聖人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非所謂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泰則侈於性,非所謂券內者行乎無名也。奢之與泰,非所謂嗇施之道也。人側而小,非正而介也。介非其屬,為辨為助,介之義也,此介所以為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則不以通物為樂,宜其不誘於物而內以自知也。若然,則性復形全而深根固柢矣。蓋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深根固柢,則復守其母。淫德侈性,豈其道哉?惟務內觀,不務外游,取足於身者,是為得之。唯施是畏,蓋與志乎期費者異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徽宗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道若大路,則道為夷矣。行不由徑,則徑為速矣。《易》言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賦周王作人亦以壽考為言,然則欲速以邀近功,其去也遠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徽宗註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疏義曰:正朝廷以正百官,則朝廷者,出治之原。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則富庶者興治之本,欲出致治之道,必在能興治之本。故舜之命契,文在於命稷播種之後,孟子言不違農時,爻在於申以孝悌之前。凡以農者,國之本也。王者所以能長且久,實本是道。然則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是為徇末棄本,非可久之道。 服文釆,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徽宗註曰: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估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疏義曰:券內者,有諸己而行之者也。券外者,無諸己而為之者也。無名者,妙道之體。期費者,有待乎物。券內者行乎無名,故取足於身而惟施是畏。券外者志乎期費,故樂通於物,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服文采,厭飲食,則恥惡衣惡食而未足與議也。帶利劍,則不知以恬惔為上也。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則非窮亦樂、通亦樂也。若是則估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徽宗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疏義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允執厭中,然後能成位乎兩間,無所偏倚,貫通上下而該之得非,建中以該上下之謂乎,得中則制命,故拔。《書》曰:建中于民。惟能用其中於民,則民不能忘。善建而不拔可知矣。 善抱者不脫, 徽宗註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疏義曰:一者,天下之至精。惟協于克一,然後能丕冒乎群動,出而交物,酬醉萬變,而應之得非,抱一以應萬變之謂乎,守一則勿失,故不脫。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惟能抱一而不離於精,則精與神合,善抱而不脫可知矣。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徽宗註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疏義曰:孟子曰:中道而立,建中而不外乎道,則能應天下以妙用。莊子曰:一之精通,抱一而不離於精,則能合天下之至神。妙用不窮,歷萬世而無弊;至神周流,妙萬物而無方。若是者,功被海宇,澤及祚裔。所施彌博,豈特行於一國之近,蓋將普及於天下。所歷彌久,豈特行於當年之頃,蓋將覃及於來世。子子孫孫保祭祀於億萬斯年之永,其傳也遠矣,寧不諒哉。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徽宗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疏義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始則修之身,終則修之天下。自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德之序也。修之身其德乃真者,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具者,精誠之至,故修之身而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書》曰:道積于厥躬。則治身以道之真可知矣。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者,蓋德既足乎己矣,以齊其家則綽有餘裕,以施諸鄉則悠久不息,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上治人者事。則治人以緒餘可知矣。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者,蓋德既分於人矣,施之邦國則充足飽滿,達之天下則兼覆廣被,所謂其土直以治天下國家也。楊子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則治天下國家以土直可知矣。其修彌遠,則德音不已,至於悠遠,所謂邇可遠在玆是也。其德彌廣,則盛德曰新,至於廣運,所謂德廣所及是也。在我者皆其真也,則真在內,所以受於天。在彼者特其末耳,則末在外,所以播之遠,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也。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皆道出而為德,所以於道為外。然則聖人以道治身而不離於真,至於修之天下,特其緒餘土直時出而應之耳。所以為真者,無所損益焉,聖人所以貴真,有在是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徽宗註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一身之微,萬物畢足,至理全於性真,天樂融於大和,其或波流,與物俱徘,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者,誠不足以明之耳。惟反身而誠,至虛而無件,至靜而勿攖,然後能內觀取足,物無不備,且將欣然自得於性命之際,其為樂莫大矣。蓋所樂在外,則其樂也小,所樂在內,則其樂也大,此反身而誠,所以為莫大之樂也。孟子之言爻及於此者,蓋以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誘然皆生,同焉皆得,以我心之所同然者,推而達之天下,則類焉者應而不失其常然之心矣。以之觀天下,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觀之為義,必上有以觀下,然後下得以觀上。以上觀下,若《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以下觀上,若《周官》所謂使萬民觀治象是也。其上下觀也如此,則從之者輕矣。《記》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正與此合。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疏義曰:夫乾確然,其道若難,而示人常易。夫坤隤然,其道若繁,而示人常簡。乾坤以易簡示人,故法象為可觀,以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也。易知而不病其難知,易從而不病其難從,則天下才理雖隱於至蹟,可以洞察而無餘蘊,又奚往而不得之哉?由是觀之,則知聖人所守彌約,所施彌博,以易簡而得之者也,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徽宗註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秉彝之民,孰不好是懿德?然與接為構,故鮮克舉之。惟民生厚,言德之根於性也,因物有、遷,則性之淪於偽矣。惟含德之厚者,然後不見異物而遷焉,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故列子曰: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氣者虛而待物,氣專則靜而不雜,與《經》所謂專氣政柔者是也。志者心之所之,志一則齊而不二,與孔子所謂若一志者是也戶氣專志一,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矣,此孟子所以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蓋盡性者,大人之事。能盡性,則實而不失其斯以虛,動而不失其所以靜,與赤子之純而不虧,真而無偽也奚擇?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徽宗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息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進世,其孰能害之? 疏義曰:世之貴於赤子者,以其靜而不變,純粹而不維,無憂患之虞,無邪氣之累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所以憂息不能入,邪氣不能襲也。憂息自外而至,故曰入。邪氣乘隙而投,故曰襲。憂息不能入,則其德全;邪氣不能襲,則神不虧。若然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不以人物利害相攖,故物莫能傷焉。物莫能傷,則無所與忤,而為虛之至矣。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蓋至虛則物無自入,如虛舟來觸,雖有褊心者,不怒也。人能致虛以遊乎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孰得而害之哉?此至人之用心若鑒,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者,亦虛而已。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 徽宗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生者德之光,能全其德,斯能全其形,斯謂德全者形全也。身者神之宇,能全其形,斯能全其神,所謂形全者神全也。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以其形生而不弊,不知所取而握固也,與夫形勞而不休則弊者異矣。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作,以合神全而不虧,不知所與而作也,與夫精用而不已則勞者異矣。自非精之至,孰能與此?蓋惟天下之至精,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之至者,可以入神,則精與神合而不離矣。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一之精通合乎天倫,人而合乎天,則亦天而已,此聖人所以貴精也。莊子論養神之道,其言有及於貴精,豈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者,有在是耶? 終日號而啞不嘎,和之至也。 徽宗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為和則氣全而啞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萬物以精化形,得一以生,玫一之謂精也。致一則不二,與《易》稱言致一也同意。精者天德之至正,保其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部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得陰陽之中,沖氣以為和也。沖氣交通而成和,與列子言沖和氣者為人同意。和者發而皆中節,得其和則氣全而嗌不嗄,所謂兄子終日嗥而隘不嗄,和之至也。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原,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蓋精者,一之所生也,受於天一之水,於方則為北,所以為智之原。和者,氣之所鍾也,得於天五之土,於位則居中,所以為信之本。人之有生,秀鍾五行,自天一至於天五,而生成之數具,誠能守其一以處其和,且將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矣。及其至也,豈不可以入神復命乎?可以入神,則妙於無方,所謂精義入神者是矣。可以復命,則歸於寂定,所謂靜曰復命者是矣。世之人所以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也,又烏知不搖其精,使之守而勿失,無暴其氣,使之純而不虧哉?於是馳其形性以傷其生,潛之萬物以汨其欲,其自棄之甚如此,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徽宗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疏義曰:和者,大同於物。關尹論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曰:是純氣之守也。能守其氣,使之純粹而不雜,則溫溫乎其和可知矣。惟其和之至,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通乎物之所造,所謂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者是也。制命在內,則造化自我,亙古今而常存;形化而性不亡,則一性常存,更萬形而不易,以挈天地,以襲氣母,得不謂之常乎?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疏義曰:《傳》曰:內視之謂明。明足以見道者,殆非目力之所及也。無形之上,獨以神視,靜而反本,朝徹見獨,則知性之在我,自古以固存也。在《易》有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以性之存,其存為道義之門,則生天生地,雖天地亦待是而生矣,詛非明足以見道,知性之不亡者,有在是耶? 益生曰祥, 徽宗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疏義曰:神示之祥,知所以應,則祥者物之先見,吉凶已兆,又烏能逃其應哉?且物之生,成理自足,從而增之,衹以為贅,如揠苗助長,勸成殆事。是皆以人助天,其禍福特未定也。惟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得其至足矣。 心使氣曰強。 徽宗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玆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疏義曰:體者,心之寓也。體合於心,則施於四體者,無非心之所根。心者,氣之君也。心合於氣,則遊心於淡,然後能合氣於漠。亢倉子謂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其於養氣之道,可謂知所本矣。惟得其所養,然後氣和而不暴,可以致其柔焉。今夫蹶者趨者,其步則不中夏武,其行則不中韶濩,無非暴氣之所為也。斯有蹶趨之不止,雖帥氣者之罪,亦心實使之而已,所以反動其心也,玆強也。以與物敵,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非自勝之道,人烏知和柔足以安物,使物莫之能傷者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徽宗註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道無古今,則生生未嘗終,形形未嘗有,莊子言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是也。物有壯老,則有生俄已實,列子言大化而曰少壯老耄是也。惟其少化壯,壯化老,斯有強弱盛衰之理,默制於造物而不得遯,是以強有時而弱,欲慮柔焉,盛有時而衰,體將休焉。役於時而為盈虛,拘於數而有多寡,豈道也哉。不道早已。 徽宗註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曰固已久。 疏義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道未始有窮也。失性於俗者,見物不見道,形化而心與之俱大惑,終身不解,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烏知道乃久,沒身不殆者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太學生江澂疏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徽宗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政者,物之精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欲言之,不可得也,故無問。蓋有門故可問,道無門也,孰得而問之?有問故可應,道無問也,孰得而應之?然則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為道者解乎此,謂道可以神受而不可以言傳,謂道可以心契而不可以迹求,於是至言去言,造忘言之妙,必以默而識之。方將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又奚事於言哉?《易》言默而成之,列子言默而得之,謂是故也。昔齧缺之問於王倪也,既問之以物之所同是,又問之以知其所不知,復問之以物無知,與夫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四問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蓋知之為淺,不知為深,知之為外,不知為內,其不知是乃真知也。若夫辮者之囿言多而未免乎累,孰知道不可言,言而非歟? 塞其兌,閉其門, 徽宗註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鍵,塞其兌則無內外之韄,和豫通而不失其兌矣。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曰以心鬥,閉其門則無心鬥之患,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矣。莊子所謂塗卻守神,《易》所謂退藏於密是也。蓋塗其卻則冥於無問,不為物誘,故能抱神以靜而與神為一,所謂塞其兌也。藏於密則復性之本,物無自而入,故能藏於天而與天為一,所謂閉其門也。廣成子曰:慎汝內,閉汝外。 挫其銳,解其紛, 徽宗註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疏義曰:銳如火之形,不能無傷,有以挫之則不傷矣。紛如絲之紛,不能無亂,有以解之則不亂矣。莊子所謂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是也。蓋深與《易》言極深而研幾之深同,以深為根,則不逐於末流,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所謂挫其銳也。約與孟子言守約而施博之約同,以約為紀,則不以博溺心,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合,所謂解其紛也。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疏義曰:和以言其不乖,同以言其不異。和其光則光而不耀,非若形碟成光者也。同其塵則大同於物,非若離世異俗者也。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已。惟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委蛇曲折,不與物逢,未嘗崖異以自處,然後能之。 是謂玄同。 徽宗註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疏利害貴賤之問為哉? 疏義曰:入於窈冥之門,祕而不示道,復乎至幽也。冥於渾淪之初,歛萬為一道,合乎至一也。復乎至幽,則藏諸用,妙而小矣,故至幽之謂玄。合乎至一,則總攝萬殊,不同同之矣。惟夫小而辮於物,得其所一而同焉,則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物我兩忘,萬物與我為一,將擇焉而不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疏利害貴賤之間為哉?凡以本無是數者故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徽宗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疏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拾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疏義曰: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自為是非,自為得失。同於己則愛之,異於己則惡之,愛惡相攻而有戚疏之態。 離乎情者則為非,離乎偽者則為是,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已用者賤失之而憂,當時者貴得之而喜,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是數者橋起片合,反復更代,一消一息,未始有極,其去道也遠矣,奚足為天下貴?則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者解乎此,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忘言而去言之之累,好非所好,惡非所惡,而泯好惡,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不可得而親疏。情非為真,偽非為妄,而忘情偽,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可得而利害。無用為用,用非有用,而離用捨,故何貴何賤,貴賤不在己,不可得而貴賤。惟知一性之有真,不見天下之有偽,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徽宗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正直為正,正者止於一也,惟止於一,則獨存常今矣,以正者道之常也。正復為奇,奇者反於正也,惟反於正,則不主故常矣,以奇者道之變也。真變於物,未始有無,真在於內,則不外從事者矣,以無事道之真也。正國何先?定於一而已。蓋國以正定故也,孟子所謂一正而國定是已。持勝有道,尚謀而已。蓋兵以奇勝故也,莊子所謂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是已。真者精誠之至,虛緣然後可以葆真,以道之真無容私焉故也。無容私則非人為之偽,順物自然而已,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經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徽宗註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政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疏義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蓋愛之利之,所以得其心也。致其所惡,則失其心也。此有以愛之,彼斯愛我矣,故親若父母。此有以利之,彼斯利我矣,故襁負其子而至焉。苟咈人以從欲,厲民以自養,致其所惡焉,則莫不相携持而去矣。然則無愛利之心,而肆虐以為威,多忌諱之禁,而苛察以為明,則不能以政裕民,民將散而之四方,百姓且不足矣,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孰知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之道乎?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徽宗註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疏義曰: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掊斗折衡而民不爭。然則存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爻有機心,所以發漢陰丈人之論也。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機械既作則機事必形,機事既形則機心必生,機心生,則昔之虛者俄且實,昔之一者俄且散,所謂無所與雜,潔而不汙者,殆或虧矣,此純白所以不備也。將見智詐相攻,巧偽日滋,或罔上以非其道者有之,此聖人有作,在宥天下,所以去此患也。 人多仗巧,奇物滋起; 徽宗註曰:仗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疏義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故先王使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慮夫末作以傷農也。至德之世,其民愚而朴,惟知日用飲食,孰有多伎巧者哉?蓋使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古之為治者,凡異服奇器鬻于市,入于宮,則國有常刑,所以敦本抑末,使斯民復敦痝淳固之俗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微宗註曰:尅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疏義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為簡髮數米,滋法令以蓋其眾,將以止盜而盜不盡矣,莊子所謂尅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蓋謂是也。蓋民愚無知,撫之則后,虐之則讎,自非以寬服民,孰肯遷善遠罪者哉?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徽宗註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疏義曰:天其運乎,惟運之以無為,故純粹不雜,職生覆而無所不覆。地其處乎,惟處之以無為,故靜止不變,職形載而無所不載。純粹而不雜,其清可知,靜止而不變,其寧可知,凡以得夫無為故也。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以兩無為相合而萬物化也。觀天地則見聖人,夫何為哉?法天地而已。夫然故暴悍勇力者化而為愿,旁僻曲私者化而為公,舉滅其賊心,皆進其獨志,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徽宗註曰:鎰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疏義曰:鎰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鬚眉可燭,鎰與水所以能若是者,以一而不變,能定能應故也。《傳》以謂鎰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蓋言其靜也。至人之用心,守靜篤而不以動違性,亦若是而已。順其自然,勿攖勿擾而已。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經曰:清靜為天下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徽宗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疏義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魚煩則漬,治民煩則惑,在宥天下,相忘於道術,如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無事而生定矣。足國裕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後之變古亂常以取禍敗者,安知富民之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徽宗註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舉賢則民相軋,故不尚賢使民不爭。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可欲矣。聖道群心之用,我無欲則同乎無欲矣。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而素樸民性得矣。蓋樸者,道之全體,未散於器者也。民復其樸,則見道不見物,而所見勝所睹。苟不能酒心去欲,方且為物紋,方且為緒使,則民失其樸,湛於人偽,尚何能還太古之風哉?老氏著書,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曰罪莫大於可欲,有曰少私寡欲,以欲之害性,不可不去之也。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不可為也,為之則偽,不可擾也,擾之則憂。惟在之使不淫其性,宥之使不遷其德,舉一世於澹漢之域,然後百姓皆謂我官然,所謂下知有之者如此。下知有之,則性不益其生,德不虧其全,舒通平泰,無欣欣之樂而親譽有所不及矣。孟子曰:王者之民,皡皡如也。其政悶悶之謂歟? 其民淳淳; 徽宗註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義曰:素樸者,民之性。能見素抱樸,然後純粹不雜,靜一不變,且至於明白入素,無為復樸焉。私欲者,民之情。能少私寡欲,然後克於勝己,善於養心,且至於背私為公,不見可欲焉。其民淳淳,莫大乎此。 其政察察, 徽宗註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疏義曰:治之要在知道,道要不煩。聖人以道在天下,由至虛以冒群實,由至靜以賓羣動,簡易而有功,未嘗簡髮數米,竊竊然以苛為明也。蓋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則弊精神於細務,勞思慮於末流也。竊竊然以苛為明,又曷足以濟世哉?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其民缺缺。 徽宗註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疏義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舉賢則民跨跂而相軋,不能定其性命之分;任智則民覬覦而相盜,不能安其性命之情。是有知有欲之為患,而民之所以遷於物也。遷於物則不足以厚民,故無全德。莊子曰:德全者形全。不能全德,則養形不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之謂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徽宗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衛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疏義曰:虛靜之中,大化密移,由隱而之顯,自無而適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是以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之生則為昭昭,而至道之極則無形也;物成生理則已有倫,而其精甚真則無形也。禍福之理,藏於幽深,應若影響,亦若化機之默運而已。惟達者知利足以生害,知樂足以生憂,乃能用智於未奔沈之初,作炳於忽眇綿之上,然後誕先登于無難之地焉。孟子慮息之戒有曰德慧術智,存乎疢疾,楊雄解嘲之論有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皆燭是理也。蓋德慧衛智可謂明哲矣,猶以存乎疢疾為心,則以君子思患而豫防故也。高明之家可以無虞矣,必以鬼瞰其室為言,則以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也。觀乎此,則於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不可不致其知也。知時無止,則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分無常,則察乎盈虛,而得失不足以攖其心;知終始之不可故,則明乎坦塗,而死生不足以累其心。無止則過而不留,無常則變而莫守,不可故則未嘗有故,是禍福之倚伏,相為消長,何常之有?所謂福為禍始,禍為福階,則以其無常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徽宗註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冬。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疏義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與若相為同異而已。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則俱是也,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則俱非也,惡能正之?是我與若皆不能相知,然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體之知安佚而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而不知正味,目之知美色而不知正色,其不得正知也。如此則是非之塗,吾烏能知其辨? 正復為奇,善復為祆。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徽宗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連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疏義曰:一氣之運,潛回於太虛之中,萬物推遷,皆在所棄籥。莊子謂通天下一氣耳,言物雖散殊,其運於氣化則一也。天下既通於一氣,則行流散徙,不主故常,今是而昨非,往者非而來者是,初無定形,先逢而後合,有所拂者有所宜,初無常分,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兩者交化,相為終始,成矣俄壤,壞矣俄成,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勢若循環,果未可定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乃一氣之自運,密移於造化,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蓋天下之生久矣,迷而不復,固非一日之積。小惑易方則以東為西,背冥山而莫之見;大惑易性,以無為有,遺玄珠而莫之求。自私之俗勝,則蔽於一曲;不明乎禍福之倚伏,則昧於至理。且復察察以治之,祇所以益其惑,不靈不解,民安得而反其真乎?是以老聘著其政悶悶篇,蓋欲使民之安常復樸,以反其真而已。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徽宗註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疏義曰:拘於方體者,常介執以異俗,所謂介於辨物者此也。介與《易》稱介于石之介同意。大方無偶,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足以應無方之傳,非若執方之謂器者矣。止而不流,言真上而無所蕩,猶水之靜止,大匠取法,所以無辨物之逵,其亦苟卿所謂能定而後能應者歟? 廉而不劌, 徽宗註曰:康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疏義曰:謹其康隅者,常矜莊以約己,所謂矜於自潔者此也。矜與《語》所謂古之矜也康之矜同義。大康不嗛,則至足無求,澹然自適,不貴苟難之行,非若康清而不信者矣。清而容物,言雖清而無所察,猶鑑之清明,應而不藏,所以無刻制之行,其亦莊子所謂勝物不傷者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徽宗註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疏義曰:亢己以為直,則直必肆其情,而陵物之態生。惟去逕庭之累,無枉撓之失,然後能直而不肆,以之應物,則周旋曲折,無所於忤,而陵物之態不生矣。悅眾以為光,則光必耀其迹,而揚行之患至。惟去形謀之光,圖滑疑之耀,然後能光而不耀,以之照用,則因時順物,未始容心,而揚行之患不至矣。是則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惟聖人乎。蓋內直者,所以徒於天。外曲者,所以徒於人。惟曲則全、枉則直者能之。用其光者,所以顯諸仁。復歸其明者,所以藏諸用。惟循有照、冥有樞者能之。蓋非聖人能和同天人神明,其德不能與此。且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不能濟以權,執一而廢百。以康為是者,如仲子之操,不能充其類,潔身以亂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知伸而不知屈,一於矯也,而不能同其波,又烏知屈伸相感,如《易》所謂利用安身者乎?微者,幽也。彰者,顯也。知彰而不知微,則一於表襮,而不能襲其明,又烏知知微知彰,如《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子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是皆蔽於曲私,不該不徧,刻意尚行,以夸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不見純全大體於天地古人之間,豈足以正天下?是未能正己而將以正人,殆不知其可也。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如斯而已。蓋聖人備道全美,抱一以為天下式,推此以表,正天下真餘事耳。此大舜所以能正眾生,無為而天下治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徽宗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臟,以腎為事,立于不貸之圃,豐智原而音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疏義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是以得於自然,無適非天,見於或使,無.適非人。聰明智識,得於自然而成於天者也,故韓非以謂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見於或使而因於人者也,故韓非以謂動靜思慮,人也。券內者以約為紀,券外者志乎期費,則其治人也,事天也,不可不以音為先焉。蓋動靜有常者,理之真。何思何慮者,道之至。適動靜之節,則動惟厥時矣。省思慮之累,則湛然常寂矣。見於或使,而在人者治之如此,可謂音也。黜聰明,然後同於大通;去智故,然後循天之理。不極聰明之力,則能收視反聽矣。不盡智識之任,則能還淳復朴矣。得於自然,而在天者治之如此,亦可謂嗇也。蓋天一生水,在人為精,腎之為藏,精所舍也。天一在藏,本以立始,故以腎為事。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於治人事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圃,而唯施是畏,豐智源而嗇出,而不侈於德。以之治人而人事治,以之事天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徽宗註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疏義曰:得性則生生不窮,失性則不能生生而窮矣。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貴於不遠復焉。迷而後復,則失性遠甚,所謂民之迷,其曰固已久矣者也,其復也晚矣。觀夫雷在地中,於卦為復,而初九言無祗悔,元吉。至於上六則為凶矣。蓋以初九之復不遠,而上六之復迷而後復也。比卦亦然,於初言有他,吉。於六言比之無首,凶。以比復好先故也。嗇則不侈於性,而去本未遠,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徽宗註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疏義曰:德者,得也。得於性之謂也。觀復於芸芸之時,適復於撓撓之際,則不離於性矣,故《易》言:復,德之本。能復其本,則性修反德,而明無不燭矣,故《易》又言:復以自知。然則不侈於性而早復,則德日起而高大矣。《書》曰:德日新,又日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徽宗註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疏義曰… 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則能勝之謂克也一德積於己,則可以至寡御至眾,命萬物而無不聽,攝天下之群動,宰制役使,無所不勝矣。《記》曰:德成而上。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徽宗註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疏義曰:德足乎己,則不蘄於勝物,而無所不勝。故在我為有裕,分人而有餘,運量酬酢,泛應而不窮,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孰知其極?孟子曰:德教沛然,溢乎四海。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徽宗註曰: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有國乎?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直以治天下。德至於同於初,則體盡無窮而得其純全,莊子所謂周盡一體者也。天下雖大,不出吾之度內,則其用天下也有餘裕矣,況於一國之小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疏義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道為萬物之母也。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心以至無心,皆由此出,故有母之義。有國之母,是有其道也,得道者無古今,雖萬世無弊,非長久而何?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徽宗註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生者,物也。生生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則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有色者,有色色者。色者,形也。色色者,性也。莊子曰:性者,生之質。劉子曰:形者,生之器。則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有國之母,則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也。復守其母,則與道為一,亘古今而常存,故殁身不殆,而可以長久。今夫草木之生,根深則柢固,猶之人也,性復則形全。惟能全其形,使形生而不弊,如草木之麗乎土,其永無窮,故與天地為常而長生,其明不息,故與日月參光而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則又超形而不與形化,離數而不與數終者也,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徽宗註曰: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漬。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疏義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是以主道治一,不知二能當一,則百事正矣。然則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固其宜也。蓋天下有常然,順之則治,擾之則憂,惟能不亂天之經,不逆物之情,法一定而不易,無朝令夕改之失,而天下治矣。猶之烹魚也,數撓之則漬,然則治大國而數變法,豈不惑哉?《傳》曰:民信其法則親。此古之善立法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不易也。然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民將無事而生定矣。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孰肯滋法令以蓋其眾哉? 以道花天下者,其鬼不神。 徽宗註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故曰其鬼不神。 疏義曰:《詩》曰:百神爾主矣。《書》曰:惟元后作民父母。莊子曰:聖人者,萬物之所係。是則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然而我忘天下易,天下兼忘我難,其所以出而經世,亦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然則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而民自化,故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而為神者,將得所憑依,得所安樂,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祟,如《詩》所謂公尸來止熏熏矣,故曰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徽宗註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道往天下,則因其固然,不擾以人為之偽,所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保民如子,視民如傷,兵革不試,故無攻戰之患,刑措不用,故無殺戮之刑。神與民兩不相傷,而明無人非,幽無鬼責,而德交歸焉,則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如《詩》所謂神之吊矣。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如《詩》所謂民之質矣,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徽宗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疏義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欲升高必自下,知高以下為基,乃不至於蹶高而無以為基。徒有趨高之心,則是好高而不為高矣,能無蹶乎?水不積不成淵,江河合水而為大,為其納眾流也,故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而流水朝宗之者,以其善下之也。然則國之所以大者,非以下流而政然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徽宗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義曰:自物觀之,惟卑故能堂,惟肖故能攘,一昧是理,恃狠乘物,將以為高,秪以取氏,蓋以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剛故也。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聖人以懦弱謙下為表,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雖不蘄勝人,而人莫能勝,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蓋知勝物之道,而自處以柔靜,物莫不為之下矣,以其靜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徽宗註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疏義曰:有歛祕有散,有盈必有虧,非特人事,天道固然。惟洞照幾先者,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知一歛一散相為消長,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知一盈一虧相為始終。故大國以下小國而以大事小,小國以下大國而以小事大,莫不各有所取焉。然則欲上人,以其言下之,而君子不欲多上人,凡以此故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徽宗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履。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疏義曰:天道以下濟,故光明而覆燾無方。地道以卑,故上行而承天時。行謙沖之道,天地且爾,況於人乎?堯以允恭而光被四表,舜以溫恭而玄德升聞,凡以法天地而已。三才異位,其道則同,是以王不自大,以法乎地,乃能無為而天下功。地不自大,以法乎天,乃能不長而萬物育。然則不自大,乃能成其大,莫不皆然。大者宜為下,不其然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二 太學生江澂疏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徽宗註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則物者道之顯歟? 疏義曰:道之為奧,其深莫測,如室之奧而深密焉,如淇之奧而深閟焉。凡戾顯而入隱,皆有所謂奧,《太元》論三摹,所以各言其奧也。且天以不見為元,西北則於卦為乾,復乎至靜,化精之所鬱也。鬱化精則氣機密移,陽遇陰而鬱矣,故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以不形為元,黃泉則深不可測,冥於至幽,魄榮之所隱也。隱魄榮則陽氣潛萌,藏其體而隱矣,故曰地奧黃泉,隱榮魄也。人以心腹為元,思慮在人,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至神之所蘊也。蘊至神則妙於無方,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人奧思慮,蘊至神也。三才異位,各有其奧。天雖有奧,而道能生天;地雖有奧,而道能生地;人雖有奧,而人在道中。所以皆冒於道,於道不可以形數求故也。三才未離於形數,而道不可以形數求,可謂難終難窮而未始有封,難測難識而莫窺其妙者也。善貸且成,其化密庸,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則自無出有,職職陳露,不得遯而皆存,物其道之顯歟? 善人之寶, 徽宗註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疏義曰:有以物為寶者,《傳》言寶珠玉是也。有以道為寶者,若此言善人之寶是也。善人不以物為寶,而所寶在道,是以自人入於天,由善達於聖,無入而不自得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人知善出於道而成於性,故其不貲之樸能利而行之也。利而行之,則好之無數,行之不怠,能盡其性,可以贊化育而配神明矣。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充實之美,積善成性也。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明自得也。若夫聖心循焉,則由是道而不違矣。寶而持之,孰大於此? 不善人之所保, 徽宗註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也而反焉,則無非傷也;無為也而動焉,則無非邪也。反無非傷也,惟去智與故,順其理而不違,然後能守其全而物莫之傷,所謂誠全而歸之是已。動無非邪也,惟虛緣葆真,靜其性而勿攖,然後能得其正而邪莫之入,所謂四六不盪,胸中則正是已。順其理而全,靜其性而正,舉天下之物,曾不足以易其守,可以保身而無危亡之憂,乃其宜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順其理,斯可以窮理;能盡其性,斯可以盡性;能保身,斯可以至於命。不善之所保,不外是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徽宗註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奧,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義曰:心居中虛靜則善,淵發於言則為風波,止則居實,見於行則為實喪。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溺於末流而非道之所貴也。然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則言美而可悅者,猶足以市;欽慎威儀,維民之則,則行尊而可尚者,猶足以加人,況體道者乎?惟體道之奧,滋發萬化,總攝眾妙,如天之運,兼覆無私,如海之容,包含不遺,彼雖紛紛自異,皆會之一理,又何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必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故惟體道者,為能盡合并之公。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徽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疏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所守至約,則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慎厥身,脩思永至,於邇可遠,在玆自脩之身。至於脩之天下,則以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故也。貴為天子,立為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將自賓,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為邦家之光,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不能有守矣。不能有守,是捨己徇人,失自治之道矣。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不如坐進此道,以自治為先故也。所謂自治非外鑠也,求諸己而已,能求諸己,則用人惟已矣。昔帝堯克明使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文王誕先登于岸,以至於以御于家邦,每得諸此。雖然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則治之要在知道也。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則以聖人者道之管也。民從之如歸市,則以聖道群心之用也。夫聖人,民之父母也。聖人尊之於上,斯民從之於下,其執犬象,天下往之謂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徽宗註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教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疏義曰:心者道之主宰,則道未始離乎我。道不可以情求,則道未始滯於物。惟不離乎我,故反而求之,自得其得,以求在我故也。惟不滯於物,故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以求在外故也。求在我者,求有益於得;求在外者,求無益於得。然則求而不得者,以道在邇而求諸遠;而善人求以得者,求在我者而已。蓋道之在我,眾美皆備,人患不求爾。誠能因心會道,則惡者可以遷善,修德罔覺,而無過舉之失,愚者可以為哲,造理而悟,無多岐之惑,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人如此,則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則以莫之爵而常自然故爾。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徽宗註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可見矣。 疏義曰:道妙於無,不可以體求,即其大全而言之,姑謂之體而已。所謂道之體,若莊子言古人之大體是也。道之體既妙於無,則寂然不動是無作也,無作故無為,無為則至為去為矣。無狀之狀是無相也,無相故無事,無事則無為事任矣。澹然自足是無欲也,無欲故無味,無味則味味者未嘗呈矣。興事造業,為之而成,雖曰有作,而為出於無為。耳目鼻口,各有所事,雖曰有相,而事出於無事。江之於味,人所同嗜,雖曰有欲,而味出於無味。以見用之所以妙也。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所以應物之有,自無適有爾,所以體道之無,至無以供其有爾。於斯三者以觀之,道之體用,果可見矣。 大小多少, 徽宗註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 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疏義曰:以物觀之,自徇殊面,壘空之與大澤,毫末之與馬體,以形異其小大而囿於形,以數差其多少而拘於數。以道觀之,萬物一體,以北海為大,曾不知大而不多,以涇流為小,曾不知小而不少,以物量無窮,不可為倪故也。若是則怨之有其辨,恩之因其心,二者雖正之器,非正之道也。施乎無報,大同於物,又烏睹其辨域?聖人以道之虛,受天下之羣實,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所以同萬有於一無,合眾小而歸之,能成其大者,天覆地載,廣乎其無不容而已。故帝王以天地為宗,而為哉中之大。 報怨以德。 徽宗註曰: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疏義曰:全德之人,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則無取於冠冕之賞,是爵祿不足以為勸也。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則無畏於斧鉞之誅,是戮恥不足以為辱也。榮辱之來,無益損乎其真,則知是非不可為分,細大不可為倪,約分之至而卒無所分矣,又何怨之有?非至德者能之乎?宜其所尚者德而已。蓋陽為德,陰為怨,報怨以德,則冥而無所辨,通而無所節,是謂出怨不怨,所以為德之上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徽宗註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義曰:《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故慮遠者不忽於其易。經曰為之於未有,故知幾者必察於其細。千丈之堤可謂川有防矣,以螻蟻之穴小而不止其潰,則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百尺之室可謂居之安矣,以突隙之煙微而不慎其焚,則熒熒不救,炎炎奈何?白圭之行堤也,必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必塗其隙,是以無火患。然則圓機之士,其作炳於忽眇綿,用智於未奔沈,每及於此,所以發韓非之論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矣。《詩》於吉日必曰慎微者,以事起於甚微故也。及其末,則不可勝圖矣。《易》於思患必曰豫防者,以其末為難圖故也。聖人智通於神,所以蚤從事者,知此而已,與苟卿所謂先事慮息謂之豫同意。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疏義曰: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然則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理宜然也。聖人躊躇興事,以每成功,所以致大治者,亦為之於小而已。《詩》稱文武之治,積小雅而為大雅,其作始也小,其成業也大,所以成內外之治,始於憂勤而已。使其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孟子舉《詩·鴟鴞》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以明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欲治之於蚤也,豈若大寒而後索衣裘者乎?然則聖人以此詩為知道者。以此,然則天下之事小可為也,大無及已。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徽宗註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疏義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則禍固多藏於微。易之者不宜,則禍固發於人之所忽。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欲不忽其微而已。聖人之應世,與民同患,至智足以周物理,遠覽· 足以照幾先,謀之未兆,常慎微以慮其始,慎終如始,而不忽人之所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也。《記》 曰:與有其己怨,寧無諾責。無輕諾之行,則言必顧行矣。《傳》曰:苟以為易,難將至矣。無多易之行,則動必迪吉矣。以此遊世,則泛應曲當,終無難矣。然所以致此,非樂通於物也,凡以無為無事無味,體道之無而已。道之所在,孰能難之?《鳧鷖》卒章言無有後艱,與此同意。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徽宗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沉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沉,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疏義曰:事隱於未然,莫不有自然之理;肇於已然,莫不有必至之機。理之所藏深矣,非至神不足以洞察;機之所發微矣,非至智不足以約知。安者危之對,有其安必危。未兆者已形之對,未兆則形泯,此理之未然者也。脆者堅之對,則堅已肇其質。微者著之對,則著已闡其端,此事之已然者也。持之於安則無危,所以能保其邦。謀之於未兆則不形,所以能防其患。聖人之知幾也,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作炳於忽眇綿,神以知來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所以能慎之於履霜。微者散之,則不至於著,所以能察之於毫末。賢人之殆庶幾也,智之於賢者,於復則不遠,於過則不二,辨之於早智之事也。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豫》之六二,當理而悟,所以為聖人之知幾。《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所以為賢人之貽庶幾。惟其知幾,故不終曰正吉。惟其殆庶幾,故無祇悔,又烏有奔壘沉流之患乎?蓋車所以陟險,航所以濟難,奔壘之車,況流之航,則聖人無所用智焉。楊雄對或人之問,所以言用智於未奔沉。然則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有終踰絕險需徒楫之之安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徽宗註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疏義曰:夫有形生於無形,凡囿於有形,莫不自微以至著,則大必滋於小也。將尋斧柯,始於毫釐之不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可知。若升高必自下,則高必基於下也。丘山崇成,始於累土之不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可知。自邇以及遠,則遠必自於近也。將致千里,積於跬步之不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可知。是三者,其作始也簡,原其始則小,其將畢也必巨,要其終則大,其理然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聖人見端而思末,所以索其至;睹指而知歸,所以要其宿。觀於遠近,默與理契,故不為福先,福亦不至,不為禍始,禍亦不來,因時而起,循理而動,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緣於有感而應之耳。彼天下之事日投吾前,將謝之而莫為,則眇綿之中固有不可不為者,然有而為之其易耶?必待於躊躇而後興,則不以易而為之也。惟不以易而為,故事之所興,咸底成績,巍乎其有成功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徽宗註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疏義曰:天下之理,可因不可為,可任不可執。為之以求成,適所以敗之;執之以求得,適所以失之。聖人體道之無,靜而無為,不從事於務也,斯無事任之責,故無敗。變而無執,不以故自持也,斯無事故之累,故無失。世之昧者,殊不知時無止,分無常,乃規度而固守之,蔽於一曲,不該不徧,是何異刻舟求劍、膠柱調瑟?宜其去道愈遠而不能趨變也,能無敗失者鮮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徽宗註曰: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疏義曰:《傳》曰:有足者可至於丘。則道必致其至,中道而止則無所至矣。又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塗必同其歸,半塗而廢則無所歸矣。仲尼有吾弗為己之語,蓋以是也,非特為學如此。雖從事者亦然,使其志猒於所守,力倦於所行,始勤而終怠,則事亦無所濟矣。始動則悅於須臾,終怠則猒於持久,凡民之情易遷於物,始動終怠,蓋莫不然。惟其止而不進,廢而自畫,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孟子興有為者之嘆,所以譬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徽宗註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疏義曰:成王戒卿士,必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動者,蓋內盡其心所謂志,外盡其力所謂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心已怠而力已疲,烏能不倦以終之哉?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惟終始惟一,故能至誠不息,圖惟厥終。惟時乃日新,故能力行不倦,雖休勿休。以此施之於事,則事必就緒而後已,何為而不成?所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者,宣其然矣。《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所過。 徽宗註曰: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眾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眾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疏義曰:莊子言次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欲利者,以物易己而汩歌於俗。列子言學者以多方喪生,則務學者,以博溺心而維學無統。夫豈足以造乎無為?夫所謂無為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而已。以物易己則喪己於物,方且與動馳,不知即動而靜。以博溺心則心枝而疑,方且為實礙,不知損實為虛。故不足以造乎無為也。聖人不然,不以利累形,求之在我也,所欲在內而不在外,欲出於不欲而已。共利為悅,共給為安,不拘一世之利為己私分,在乎兼足天下焉,正莊子所謂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則去人為之偽也。所學在心而不在進,學在於不學而已。因性所有,習以成之,不以支離曼衍益其真,期於朝徹見獨焉,正《詩》所謂學有緝熙於光明也,故以復眾人之所過。蓋窮巧極珍,難得之貨也。聖人不貴之者,欲使民不遷於物而已,可謂我無欲而民自足矣。捨本趨末,眾人之所過也。聖人以復其過者,欲救其過,使歸諸道而已,可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矣。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賢人則異乎眾人,賢者之智,猶有所謂過,況眾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則性脩反德,德至而同於初,將至於見道而絕學,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此絕學所以無憂也。若顏氏之子忘仁義禮樂,而簞瓢捽茹不改其樂,其於聖人樂以忘憂,為殆庶幾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徽宗註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疏義曰:天運乎上,不產而化,地處乎下,不長而育,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動若植,萌區異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萬物得由其道者,豈或使之?其生化形色,智力消息,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則不益生,不勸成,因其固然,付之自爾,故能成其性也。然而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所以成其性者,豈假人力為之哉?為者敗之,且有助長之失,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也。恃道化則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不任智巧則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將無為而萬物化矣。彼刻楮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鮮矣,何足以語道化之妙。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徽宗註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為,而悅夫哼哼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善貸曲成而其仁顯,故民可使由之。巧妙功深而其用藏,故不可使知之。 《易》所謂百姓曰用而不知,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是也。古之善為道者,每得乎此,以謂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推此以化民,則民莫不由之。得之於觀感,反其常然,而復性之本,將以愚之也。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故無所施其智巧焉。蓋天下有常然,曲直無待於鈞繩,圓方無待於規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相忘於道術,而去其智巧之心,斯不失其常然矣。自非善為道者,何以臻此?三代而下,釋夫恬惔無為,而不知處無為之事,悅夫哼哼之意,而不知行不言之教。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而失之戕賊,是待鈞繩規矩而後正也。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過於村傴,是待繩約膠漆而後固也。若是則失其常然矣,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蓋明民而治之,非所以治天下。惟在之宥之,則民日趨於平泰之域,無事而生定矣,又何治天下?以感子之心為,故曰有治天下者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徽宗註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義曰:弓弩畢弋之知多,則羽而雲翔者不能高至。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鱗而川泳者不能趨深。削格羅落置眾之知多,則足而蹠實者不能走壙。在物尚此,況於人乎?故知詐之變多,則俗惑於辮。莊周即物理以驗人事,則知萬物皆由於道,而不可擾之以智,所以言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也。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以道之虛靜,出為天下應耳,又何智之足為?是以善言治者,論太平之本則曰智謀不用,語道化之妙則曰不恃智巧,豈非治之要者在知道而不在於好智者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徽宗註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疏義曰:莊子曰:智者,爭之器。智出乎爭,則民多逐利而機巧。所謂法出者,非法不足以繩之也,嚴為法禁,容有抵冒,而生姦宄之心者不能齊也。所謂令下者,非令不足以號之也,令出惟行,容有面革,而起詐偽之情者不能止也。經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則姦詐可知,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徽宗註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疏義曰:莊子曰:道者,為之公。以道為公,則民皆不約而自孚。所謂焚符破璽,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所謂剖斗折衡,非掊而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無所用也。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民正而足,則其朴鄙不爭可知,所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徽宗註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疏義曰:表正則影正,源清則流清,自然之符也。聖人位乎民物之上,端表澄源,無為而天下化,明夫用智與不用智而已。知此兩者,則知治國責清靜而無俟於用智也。不以智治,則聽唱視儀者,得效法於觀感之際,孰不則而象之以為楷式哉?蓋則猶作則之則,以其有則則之也;象猶垂象之象,以其有象象之也。惟其有則象,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若苟卿設為國之問有曰槃圓而水圓,盂方而水方,意與此同。 常智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徽宗註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疏義曰:妙而小之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常知楷式而不用智,則以抱一為天下式也。若然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宜其與天合德,無聲無臭,深不可測,無際無分,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若列子所謂疑獨者是已,故曰與物反矣。自非入而辮物,與天合德者,疇克爾哉? 然後乃至大順。 徽宗註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疏義曰:在《易》之《豫》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順者天之理也,自其體而言,則乾為至健,即其理以觀,則乾以易知,故曰易簡天下之理得,此順所以為天之理者歟?乃至大順者,去使然之智故,即自然之至理,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者此也。莊周著《天地篇》論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有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合則通於天地,同乃虛而已。緡緡相合,非薪合而合也,非有所知見而合也。若愚則冥心而無知,若昏則膠目而無見,無知無見,是謂玄德。德至於玄,則性天自然,無所與逢,而同乎大順矣。惟其若愚若昏,所以能去智;惟其去智,所以能原於德而成於天。莊子於《天地篇》之首言天德而已矣,意與此合。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徽宗註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疏義曰:帝言德,王言業,此興事造業,所以為王。公乃王,王乃天,此其一上比,所以為王。王有歸往之義,所謂下民之王者是也。下民所以嚮往而親附之者,以其容而下之,有下下之道故也。是以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也。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民之歸往,豈不相似。然天保序言君能下下,而《詩》言無不爾哉,承其知善下之道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徽宗註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眾。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猒。《易》曰:百姓與能。 疏義曰:貴以賤為本,故《易》於《屯》言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雲雷並作,於卦為屯,天造草昧之時也。初九為經綸之君,能以謙自牧,忘其貴而下下,民之所求也,所以能大得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是豈教誥之所能令哉?以其言下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彼皆有願戴之心,而從之也輕,若孟子言從之者如歸市是已。以其身下之,故處前而人不害,彼皆有樂附之誠,而利之者眾,若莊子言利仁義者眾是已。然則四方之民莫不親之若父母,愛之若芝蘭,無思不服,得之於心,悅樂推而不耿矣。《易》曰:百姓與能。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以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則親譽之至宜無時而斁矣。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疏義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猶能得人,況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固宜為人之所愛,宜乎陽子居有是言也。蓋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則能處乎不爭之地。安往而不愛,則物不能與之爭矣。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徽宗註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疏義曰:肖人者其體小,故肖物者小。大者人之所因,故為物所肖者大。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由七十子以觀仲尼,則小大固可知已。然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其得道之本宗焉。夫道覆載萬物者也,以道為萬物祖,故有萬不同,莫不由之,天地雖大,秋毫雖小,皆不外於覆載之內。所謂洋洋乎大哉,言其無不該徧,廣乎能容也。為物所肖而非肖物,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可名於小,豈得為大乎?自道之外,何物之有?即未始有對言之,固不可以議,其將強為之名曰大爾。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徽宗註曰:異乎俗世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疏義曰:聖人則異賢人矣,以賢視聖,猶有所異,況世俗之見?其異之也,固亦遠矣。所謂三寶者,在世俗則蔽於私見,妄以為小,殊不知即理以觀,乃所以為大也。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則善抱而不脫,未始須臾離也,可謂寶而持之矣。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則知我有三寶,在內不在外,持之不可不至也。惜夫世俗之人,知寶其寶,而不知寶其所以寶,適為身之累,是以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一曰慈, 徽宗註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疏義曰:慈以惠物為心,仁以愛人為本,故天倫以父慈為先,燕飲以慈惠為示,要之皆本於愛也,得非慈為仁之實乎?老君言道德,絕仁而寶此,曾非絕之也,欲明仁之實而已。 二曰儉, 徽宗註曰: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疏義曰:儉者德之共,禮於用貴稱,故儉不中禮則徧急,儉而用禮則適宜,要之皆貴於足用也,得非儉為禮之節乎?孔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非嗇之也,欲明禮之節而已。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徽宗註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柔則不求勝人,以濡弱謙下為表,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剛則求勝人,雖以出眾為心,曷常出乎眾哉?苟或能剛不能柔,為先以求勝人,是尚力而不貴德也。力者爭之端,尚力則好勇,而物與之敵,若莊子所謂以巧鬥力是也。謙者德之柄,貴德則柔巽,而物莫能賤,若《易》言天地人神皆取於謙是也。然則求勝人者,尚力而不貴德,孰若不求勝人者,貴德而不尚力哉?能不尚力,則知不敢為天下先,能謙抑而進於德矣,是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 夫慈,故能勇; 徽宗註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故愛人者惡人之害也。有德者必有威,故有常德足以立武事也。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稱其視民如傷,可謂能慈矣。逮至赫赫斯怒,以整其旅,有武功以伐于崇,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勇莫能加也。慈故能勇,有見於是。 儉,故能廣; 徽宗註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疏義曰:《易》曰:坎為隱伏。坎以方則北,於時為冬,萬物之所歸也,故伏藏者又於冬言之。又曰:震為蕃鮮。震以方則東,於時為春,萬物之所出也,故蕃鮮者必於春言之。 惟閉藏於冬,然後蕃鮮於春,一氣之運而萬物之理,其消長自有時,其盈縮自有數,贍足一切而未嘗侈,化出萬有而未嘗費,天地尚然,況於人乎?且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觀夫坤為吝音,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則知天地不能常侈常費可知矣。惟其無所侈費,所以能致其廣大,驗之人事,亦若儉故能廣而已。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徽宗註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疏義曰:天為萬物父,化貸覆育,默旋於太虛之中,職職羣動,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逆,順物自然,因其成理而已。然囿於生成之數者,咸於此受命,而不能外其棄籥,則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矣。道之尊,首出庶物,而天下莫能卑,故為器之長。老氏於知雄守雌亦曰: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蓋聖人體道之無虛,己以遊世,處乎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大道已行矣,豈非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徽宗註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眾,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疏義曰:三寶者,一性之真,非人為之偽也,惟物我兩忘,然後能寶而持之。世之人拾真逐偽,昧於至理,以我敵物,與接為搆,知勇之足以勝人,以力相誇,而不知慈乃能勇,有所謂七者無敵。知廣之可以夸眾,以侈相靡,而不知檢乃能廣,有所謂用之不可既。知器長之足尚,以能 相矜,而不知自後之為要,有所謂自後者人先之。是皆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故曰堅強者死之徒也。昔莊周論博大真人有曰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則慈可知矣;有曰徐而不費,以約為紀,則儉可知矣;有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則不敢為天下先可知矣。若老氏者,可謂能允蹈之,其於垂訓,非獨載之空言,又見於行事。世之人乃拾此而謂剛強,危其身亦弗思之甚也,真所謂蔽蒙之民。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徽宗註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疏義曰:孟子曰: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民之所好在於七也。仁者無敵,則能興大利,致大順,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故以戰則勝,而舉萬全之功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荀子所謂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然則效死勿去,以守則固者,以民之所懷在於仁也。昔成湯克寬克仁,乃能敷奏其勇,而莫敢不來享,是仁人無敵於天下也。太王有至仁,故邠人從之如歸市,是民愛其上也。在上者以德行仁而無敵,在下者心悅誠服而愛上,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慈之為寶,豈小補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徽宗註曰: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疏義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仁根於心性所有,天所命也。惟體仁則能盡性,惟盡性則能得天,故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所謂栽者培之,善者福之,作善降之百祥之類是也。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所謂傾者覆之,禍者淫之,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是也。然則繼道者善,首善者仁,天道無私,常予善人,所以救之使安,衛之使固者,以其善於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又以見仁為百善之總名,人道之大成也,好仁者無以尚之。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二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太學生江澂疏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徽宗註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此武所以為下道也。士志於道,故以尚志為先。《記》曰:士先志。莊子曰:賢士尚志。皆謂士之所事,在乎抗高明之志,不以德之末為務也。志之所尚,請循其本曰仁義而已。居仁之安宅,則有不忍人之心,故殺一無罪,非仁也。由義之正路,則義然後取,故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善為士者不武,亦惡夫殺之傷吾仁,取之害吾義而已。孔子之垂訓亦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則士志於道,可不務本而由仁義行乎?此仲由能勇不能怯,所以得罪於聖人之門。 善戰者不怒, 徽宗註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疏義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強誠在。夫聖武布昭,速不疾而至不行;神武不殺,幽無形而深不測。運籌次勝,收功於萬里,雖有智者無所用謀,蓋如兵法有取於上兵伐謀,固不戰而屈人兵矣,又奚待抗兵相加而遷於怒哉?蓋五行之理木勝土,則七情之中怒勝思。所謂怒實勝思者,以其非良心也,累於物為所使焉。然則上兵伐謀,固無俟於怒也。文王所以赫斯怒者,特人怒亦怒耳。人怒亦怒,是乃所以與民同息,而異乎人之私怒也。若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者也。惟明乎此,然後可以言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徽宗註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疏義曰: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順民之心,從民之欲而已,此爭所以為逆德也。爭則強戰而嗜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而不知禦外侮,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而不知消內患。若然則代翕代張,相為雌雄,勝敗特未定也。惟善為士者,不武所以成其武,故仁無不懷,義無不畏,有所謂征之以仁義者矣。惟善戰者,不怒所以濟其怒,故動而有名,出而有功,若所謂不怒而威者矣。惟善勝敵者,不爭所以弭其爭,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有所謂不爭而善勝者矣。以此保大定功,安民和眾,武之七德於是乎在。信斯三者,皆出于德。既出于德,則其盡善可知,故曰善。此有常德以立武事,所以為常武之美者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徽宗註曰: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辮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辮者為之使。 疏義曰:任道者無為而尊,任事者有為而累。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任道者也。下必有為,為天下用,任事者也。惟其任道,則任事者為之責。惟其無為,則有為者為之用。是以聖人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謂之落天地,則智通於神矣,不自慮則用人之智,故智者為之謀,所謂至智不謀是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不自為則用人之能,故能者為之役,所謂大巧若拙是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不自說則用人之辮,故辯者為之使,所謂大辯不言是也。夫如是,則不自用而人樂為之用矣。 是謂不爭之德, 徽宗註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疏義曰:成和之脩,內保而不蕩,何事於名?智者以恬相養,和理出於性,何事於爭?德蕩乎名,彼亦以名勝我矣。智出乎爭,彼亦以智與我爭矣。惟才全而德不形者,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然後無名爭之累焉。何謂才全?不滑其和,而與物為春。何謂德不形?勿失其性,而德同於初。獨立乎不爭之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若哀馳他之和而不唱,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故仲尼言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人而已矣。非不爭之德,何以與此? 是謂用人之力, 徽宗註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疏義曰:司耳目之任者,必有聰明以竭其視聽。蓋視之辮者,以明為先,聽之察者,以聰為貴,惟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然後足以周事物之情。當心膂之寄者,必有智力以盡其謀能。蓋謀之善者,其智無壅,能之善者,其力無倦,惟內能用其智,外能勤其力,然後足以收功業之效。聖人廣覽兼聽,任賢使能,其視聰明智力特餘事耳,所以用天下而不自用者,以其體道之無為故也。《傳》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所謂位之者無知也,宣其然乎?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徽宗註曰: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疏義曰:天無為以之清,而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無為為之之謂天。聖人處無為之事,則與天合德,不爭而用人,猶太虛寥廓,造,化密移,付六子之自運而已,故可以配天。記禮者稱高明配天,必繼之以無為而成,是與天合德者也。與天合德,則上與造物者遊,而超出萬有,是謂可以配天,若是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蓋極言其至也,若太極者,則以高為至,若無極者,則以遠為至,所謂屋極者,言木之至而已。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徽宗註曰: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疏義曰:聖人之武,力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智極神明而人莫窺其奧,其於命將俱師出而與民同患者,感之斯應,亦不敢取強焉。惟不以強勝人,故以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則其動也時,所謂兵戢而時動者是矣。不得已而後起,則其起也果而不得已,所謂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者是矣。若然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為應兵,應兵為客者也。為客則示之以綿綿之弱,與孫子所謂善勝者立於不勝之地同意。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徽宗註曰: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疏義曰:冒矢石,臨鋒鏑,以器則凶,以事則危,豈得已而用之哉?將以禁暴戢兵,安民和眾而已。制字之義,於戎則貴其自保,於武則取其止戈,未始以樂殺為心也。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難進以言其有所守,非怯於進也,知以守則固而已。易退以言其有所戒,非勇於退也,不趨利犯難而已。《大司馬》閑戰陣之法,於田獵之間教以坐作進退,有疾徐疏密之節,或以鼓進則鳴鐲以節之,或以鼓退則鳴鐃以止之,況於赴敵,可不慎其進退之機乎?兵法曰:不動如山,取其止而能靜。又曰:其疾如風,取其疾而能速。惟明乎此,然後能知用兵者之深意於不敢進寸而退尺,是為得之。 是謂行無行, 徽宗註曰: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疏義曰:武於道為下,於德為末,士志於道而據於德者,故善為士者不武。又況三軍五兵,爻須精神心衛之運動而後從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則武豈可覿哉?宜其行而無述,在武志而不在武事,妙而不可以邊觀,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者歟? 攘無臂, 徽宗註曰:善戰者不怒。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雖不怒而威。《詩》曰:如震如怒。謂之如怒,則怒出於不怒,是謂善戰者不怒。 仍無敵, 徽宗註曰:善勝敵者不爭。 疏義曰:仁者無敵,雖不爭而勝。《詩》曰:時靡有爭。夫惟不爭,故人亦弭其爭,是謂善勝敵者不爭。 執無兵。 徽宗註曰: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為先,用兵以人和為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用人之力而已,又何事於執兵哉?孟子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為弧矢以威天下,則威天下非不以兵革之利也。以本勝末,言之在用力而不在兵革,所謂無事於執兵者如此。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徽宗註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疏義曰:敵之不可輕也久矣,古之善用兵者,貴夫量敵而後進,戒在於輕敵故也。觀《采薇》之師,於一月三捷,則言我之能勝敵;於小人所腓,則言敵之不能勝我。我雖能勝敵,敵雖不能勝我,猶不忘於日戒,則敵果可輕乎?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惟其樂殺人,則喪其慈,而不能寶而持之矣。捨其慈且勇,則於民不能施仁,於物不能博愛,而失仁民愛物之心,是以不可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疏義曰:聖人家天下,子兆民,天覆地載,海涵春育,豈使斯民墮塗炭,而不為之禁暴哉?於是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則虐民者有所不容也。自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孰能與此?蓋神武不殺者,不以威形服萬物也,是致是附,懷之以德,而以慈為寶爾。然所謂德者,仁義而已。故七者愛人,惡人之害之也,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所謂懷于有仁是也。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所謂德威惟畏是也。然則既曰以慈為寶,又曰仁無不懷,義無不畏者,何耶?蓋由仁義行則威愛兼濟,慈故能勇矣,與莊周言薰然慈仁,而不忘於以仁為恩,以義為理同意。惟仁無不懷,義無不畏,則民之歸之,心悅誠服,其於次勝真餘事耳,是謂常勝,不其然乎?昔成湯以不競不絿敷其政,則仁之事盡矣,以不震不動奏其勇,則義之事盡矣,七義兩盡,故能動而不括,而收莫我敢曷之效,豈非常勝之道有在於七義耶?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徽宗註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欺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疏義曰:道則高矣美矣,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昭若日星,所以甚易知。道一以貫之,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畫若準繩,所以甚易行。即六經之說以明之,則知道之較且易也。如溫柔敦厚《詩》之教,疏通知遠《書》之教,以至廣博易良,潔靜精微,恭儉莊欽,屬辭比事,無非載之官也。因其言以求其旨,則知之非難矣。《詩》以導志,《書》以導事,以至導行,導和,導陰陽,導名分,無非見之事也。因其事以導其法,則行之非難矣。.善夫孟子之言,有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蓋道者,人所共由,猶大路也,出入往來,不外是焉。天下無不能,有欺不能者,失之.冥行而已,惑多岐者有之,好小徑者有之,或自崖而反,或半塗而廢,皆弗思之甚也,其所以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使其知人人有貴於己,能反而求之,則道在邇,不必求之遠,而道將為汝居矣。老子垂教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誠歌使天下後世皆知求諸己,深造之以道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徽宗註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疏義曰:心聲之發,自無適有,不能以巧歷計,是言不勝窮也。故寓之筌蹄,無非言者,理雖非荃蹄之可盡,然未始外於荃蹄,則言者理為之本也。機務之繁,日馳無窮,不可以為量數,是事不勝應也。故涉於度數,無非事者,道雖非度數之可求,然未始離於度數,則事者道為之主也。莊子曰:兩家之議,孰偏於其理議?言其義必歸於至理,則言以理為本可知。然理必謂之本者,與所謂請循其本同意。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事之所兼,進而至於道,則事以道為主可知。然道叉謂之主,與所謂要在於主同意。夫理可因而不可違,惟順理而索,求則得之,使恬然理順,然後言當於理,可遵而不可失。惟循道而行,亦允蹈之,使心與道會,然後事合於道,言當於理。事合於道,操此以為驗,稽此以為次,無施而不可,天下無難矣。謂之易知易行,寧不諒哉?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徽宗註曰:小夫知之,不離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疏義曰:一心虛靜,遠近可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則智亦大矣。小夫之智,蔽於己私,其所知曾不離于竿牘,是弊精神乎蹇淺。彼其有智,不出乎四域,特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何足以知道?非道不可以政知,以其知不能及之故也。莊子曰:知道易。惟玄覽達識,以不知為真知,然後能有知。彼小智自私,未免乎累,求其知道,厥惟艱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徽宗註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眾,有獨智之慮者,見驚于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疏義曰:出類拔萃,高世之行也。有高世之行,殆非世俗之所識,故見非於眾,以眾之常情,私於好惡而已。存神索至,獨智之慮也。有獨智之慮,殆非小智之所及,故見驁於民,以民之至愚,淪於蔽蒙而已。非者以異而為非,驁者以敖而為驁,若鷽鳩笑南淇之進,井蛙薄東海之樂,多見其不知量也。求其所以然者,蔽於一曲,明不足以致知而已。《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使單見淺識皆足以知道,則何貴於道哉?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記》言有以少為貴者,誠在夫知我者稀,故為天下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徽宗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街鬻。 疏義曰:道之妙物未嘗顯,物之由道未嘗知。聖人者,道之極也,入而徒於天,其藏深矣。自其全於天而言之,所循者天理,所休者天均,行而無進則為天遊,動而無吵則為天機,觀天而不助,樂天而無憂,是皆以天合天,妙用無用,不啻若善,力而藏之,是藏於天者也。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有時而遯。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可謂密矣,有時而失。以所藏在物而不在道也。聖人復性之本,與天為一,其亦異於此矣,夫豈樂從事於務,以自衒鬻為心哉?衒之飾行,與衒玉而賈石之衒同。鬻之自售,與幫技而得金之鬻同。不自街鬻,則太白若辱,盛德若愚,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宜季咸無得而相。 知不知,尚矣; 徽宗註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疏義曰:出而交物,為無所至,入而辨焉,為有所至,道之所以為至者,則入而辨於物也。入而辮於物,殆不可以知知,況其窈窈冥冥,會於渾淪之中,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者乎?況其昏昏默默,隱於言意之表,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者乎?孰謂知之可以索其至哉?廣成子所謂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則以道非知之所能知故也。泰清問乎無窮則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則曰吾知,道以此兩者為孰是孰非?是未明夫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之理,此所以有深淺內外之辮,是以言知之外矣,不知內矣,不知淺矣,知之深矣#1者也。惟知不知之知,然後為真知。若然則造形而上出有無之表,而超然不與物偶,可以心契而默識焉。天下之物,孰尚於此?故曰知不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徽宗註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而曰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疏義曰:明以虛政,覺以靜生。泰定之宇,初無纖翳,妄見一投,則虛靜者俄遷於事物,倀倀然所知者粗而不知其至精,所知者末而不知其至極,是皆以不知知者爾之人也。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而日淪於憂息之域,其為病孰甚,又烏得達觀之士為之發藥,使去八疵四患,淵然自得於泰定之宇哉?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疏義曰:愚則無知而不智,惑則多疑而昧理,皆性之病也。性之病,與孔子所謂民有三疾同意。惟知此而辮焉,故能解其蔽,袪其惑,莊子以謂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以是故爾。蓋知其愚,知其惑,所謂病者能言其病;非大愚,非大惑,所謂病病者,猶未病也。苟或不知出此愚而好合用,而兩疑以惑,則亦終身不靈不解而已。此南榮越自知其病,未能勝大道之藥,所以願聞衛生之經也。然則病其所病,斯不病已。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疏義曰: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往不存,惟能素逝,則不蘄通於事,而事無不通矣,則以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也。蓋本原者,道之體。惟先立其大者,則與神為一,疏觀坐照,無所不達,有真知也。常若不知,夫孰足以息心已。莊子以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為王德之人,以是故爾。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徽宗註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疏義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捨真逐妄,外悅紛華,交戰於利害之塗而恬不知懼,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莊子所謂宵人之罹外刑,《易》所謂荷校滅耳,凶,此也。迹其所為得,非不畏其威致然耶? 無狹其所居, 徽宗註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疏義曰:泰定之宇,充滿天地而莫窮其畛域,周流六虛而莫究其端倪,則一性之宅,至大而不可圍,恢恢乎有餘地矣。世之昧者,蔽於一曲,見物不見道,妄鑿垣墻而植蓬蒿,而其居始狹,以曲士不可以語道故也。欲其廣大流通而復性之常,必有為之發節者,然後礙者斯達,塞者斯通,擴而充之,且將上際下蟠而彌滿天地,無不覆冒而包裹六極,其居為廣居,而未嘗狹隘褊小矣。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亦以不狹其居故也。莊子曰: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蓋以道降而愈下,而居且狹故也。 無厭其所生。 徽宗註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曰一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夭者,無猒其所生故也。 疏義曰:人之生也,雜乎芒茹,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生者,一氣之暫聚也。凡受陰陽之氣以成形者,夜則靜與陰同止,入而與物辮,晝則動與陽同作,出而與物交,人之生固已通乎晝夜之道,而與物之所造同矣。是故與物辯則萬慮息而嚮晦,與物交則萬緒起而泛應,苟不知存生以自衛,而多方以喪生,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是也。梏之反覆不一,雖夜氣且不足以存,其勿喪良心亦云鮮矣。惟純氣之守者,以直養而無害,則天地之大和,足以保之使勿散,合之使勿離矣。夫然故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曷有中道之夭哉?非無猒其所生,曷致是耶? 夫惟不猒,是以不猒。 徽宗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疏義曰:榮辱之來,必象其德,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則善惡之報,殃慶各以其類至,未有不自己求之者也。然則秀鍾五行,靈備萬物,賦自然之性者,欲致其生之不猒,誠不可自猒其生也。昔封人為禾,耕而鹵莽,耘而滅裂,乃各隨其所報,及深耕而熟耰,則其禾繁以滋。孰謂治形理心,不有似封人之所謂歟?善養生者,宜解乎此。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疏義曰:自知者明,聖人有自知之明,雖旁燭無疆,豈自見以矜我哉?惟不自見以矜其能,乃所以為知之盛,自見者不明故也。自愛者仁之至,聖人有自愛之仁,雖博施濟眾,豈自貴以賤物哉?惟不自貴以臨物,所以為愛之至,自後者人先之故也。以是御人羣,斯能措天下安平泰,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宜其樂天以保天下,而無威怒之足畏歟?聖人去彼取此,夫豈外於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者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徽宗註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疏義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剛強所以為死之徒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柔弱所以為生之徒也。世之人徒知勇於敢,毅然有進而不顧,曾不知至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堅,所以為道之用者,獨存而常今也。子路遊聖人之門,乃不知道之用,而未免乎行行之強,能勇不能怯,又何所取材哉?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若夫知雄守雌者,非不能勇於敢也,蓋其自處乎柔靜,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將復歸於嬰兒,可謂勇於不敢則活也。此廣成子處其和,以脩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者,以勇於不敢故也。《傳》曰:自後者,人先之。勇於不敢,則知持後之道矣。能持後則能處先,惟知常勝之道在柔者,可以語此。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徽宗註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疏義曰:人所謂到於道為倒,道所謂到於人為倒。勇於敢者若有所利,天實害之。勇於不敢者若有所害,天實利之。蓋天下之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相為代謝,相為消長,自然而然也。知此兩者,則利害之理判然明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徽宗註曰:畸於人者,伴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疏義曰:人不勝天久矣,蔽於人而不知天者,方且以人勝天,任情而行昧。夫天之所惡,鳥能畸於人而侔於天哉?然則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自然之理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徽宗註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疏義曰:惠迪吉,故順天者存;從逆凶,故逆天者亡。知人之所為,不可不知天之所為也。莊子曰: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白+臯)天不宜。聖人與天為徒,配神明而贊化育,宜無所難也,猶不敢多易,況其下者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徽宗註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逢,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疏義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唯運而無積,故能斡旋萬物,自無出有,陽以熙之,萬彙以滋,則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陰以肅之,萬物以成,則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逢。宰制維綱,千變萬化,獨立於不爭之地,殆見俄消俄息,一滿一虛,任一氣之自運而已。且萬物雖多有,不能逃其樞,所以生成稟貸,職職萬狀,咸於此受命,則善勝之道,孰過於此? 不言而善應, 徽宗註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疏義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也。福善禍淫者,天道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造化密移,潛運於太虛之中,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變化者,殆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必因其時。所以示人者,殆見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必從其類。原其赴感之速,無毫釐之差,直若影之隨形,響之從聲,未嘗私於所應,天何言哉? 不召而自來, 徽宗註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疏義曰:乾為君,首出庶物者也;為父,萬物資始者也。臣受命於君,子聽命於父,是出命者能召之矣。惟有以出命,故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凡有生之類紛錯於不可為量數之中者,皆無得而召之也。無得而召,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周行不殆,斡旋於冥寞之中,造化密-移,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坦然而善謀。 徽宗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疏義曰:常易者,坦然也。知險者,善謀也。乾積三陽以成體,此之謂至健。若健若難,而德行常易以知險,雖陰之險不能陷也。《易》於《上繫》言乾以易知,於《乾》之上九知一陰之將生,則能用九而吉,非坦然而善謀之謂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徽宗註曰: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疏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疏義曰:天任理,人任情。任情者,私於己見,雖密而不徧察,所以有間。任理者,公於大同,雖疏而不得逐,所以無間。則密而有間,人所為也。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各應其類,未始或失,豈天網有意於是哉?其於禍福也,因彼固然,咸其自取爾。世之人蔽於一曲,闇於大理,逐末忘本,觸途生患,殊不知天道昭昭,常與善人,而惡者亦無所竄其察也。且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至矣。爭而後勝,言而後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皆人也。人而不能天者,乃小智自私爾。使民去此之智,即彼之理,庸詛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惟聖人乃能體此,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若天之不爭而善勝;行不言之教,若天之不言而善應;效物而動,不行而至,若天之不召而自來;平易恬惔,其神若卜,若天之坦然而善謀。是聖人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宜其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也。是篇始言勇於敢者人也,終言疏而不失者天也,聖人之合天德,固異乎眾人之勇於敢,所以始終言之者,蓋將以發明天下後世也,學者宜加思焉。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徽宗註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央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疏義曰:民之初生,本無殊賦,太易與之神,太素與之性,為萬物之靈,為天地之貴,夫孰不知悅生而惡死?水不何蔽蒙者易遷於物,因無常心。苟無常心,則抵法冒禁,無不為己,及陷乎罪,則刑戮隨之,則是民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者也。惟聖人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樂其生,陶陶然遷善遠罪,玆用不犯于有司,而刑措不用矣。其有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次焉,抵冒而終不化者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徽宗註曰: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疏義曰:民既樂其生,則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而以犯法為重。由是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言必有物,而奇言者息,知奇言有誅故也,行必有常,而異行者珍,知異行有禁故也。執而殺之,國有常憲,求其抵冒者,吾未知其有敢。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者,正此意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者斲。 徽宗註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疏義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無為而尊,故用天下;任事者有為而累,故為天下用。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惟分各有常而不易,故典獄則有司殺,運斤則有大匠,君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彼從事於務者,未嘗過而問焉,使下有為也,上亦有為,是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安能治人哉,然則倒道而言,逢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聖人之治,無為而天下功,所以得治之要者,在知道而已。知道則為無為,事無事,而天下為用焉。是以文王能宅俊而官,使之於庶言庶獄庶慎無所兼,惟以得有司之牧夫為急,則其無所代可知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徽宗註曰:代新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疏義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措天下於安平泰,又惡有代斲之傷乎?此莊子於《應帝王》則曰:無為事任。是無為而任事者責也。宜其於篇終乃曰:至人之用心若鑒,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竟 #1不知淺矣,知之深矣:疑作『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太學生江澂疏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徽宗註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疏義曰: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使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曰用飲食,樂歲終身飽者,非特不重其賦,以養民而已,蓋有以使之棄末趨本故也。蓋德惟善政,而政所以裕民,治古之時有得於此,是以即十有二土以辨其宜,因十有二壤以教其稼,分地職,奠地貢,任之成功則有鄙師之賞,勸之弗率則有載師之罰,未然故民莫不致力南畝,樂業勸功,而黎民不饑矣。當是時,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又焉有田萊多荒,不足於食之患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徽宗註曰: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以政事治之,雖應物之有,常體道之無,即其酬醉之用,不離於淵虛之宗,好靜而民自正,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所以然者,以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故也。恃道化則政不煩,不恃智巧則姦偽息,民將復歸於樸矣。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之謂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徽宗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疏義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世之人不知,取所重,遺所輕,乃厚於其生,薄於其義,苟得於利者,靡不為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動,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至於失其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方且蹈犯艱險,輕於視死,雖矜生太厚,適足以喪生也。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歛,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疏義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即一身之所繫,莫若乎生,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惟不自有其生,乃能全其生,則達生之情者,又安用務生之所無以為哉?悲夫世之人以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殊不知無累則正平,正平則邪氣不能襲,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矣。能無累則無以生為,無以生為則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可以棄事而遺生矣。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德同於初,則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貴生雖異於輕死,不若遺生則又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歛,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釿鋸不用,椎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無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民足食而不飢,民復樸而不難治,民貴生而不輕死也,帝王之極功,其在是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徽宗註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義曰:列子曰: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萬物盈於天地之間,麗於奇耦,域於動靜,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即其生殺言之,陽氣常熙以發生為德,萬物因之以敷榮,故柔者剛,弱者強。陰氣常凝以肅殺為事,萬物因之以凋瘁,故堅者毀,銳者挫。氣機密移,至於肅殺,則沖和喪而復乎至幽矣。世之役於陰陽者,知其生殺相代,而不知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故失生理而動之死地焉。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莫不由之者也。計事則堅強足以勝柔弱,語道則柔弱足以勝堅強,此堅強為死之徒,柔弱為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 徽宗註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運精神,動心術,所務者本,而後末從之,則天威震疊,神武不殺,見於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固足以保大定功,安民和眾,得其常勝之道,又豈以兵強為先哉?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然則抗兵相加而哀者勝,以善持勝故也。 木強則共。 徽宗註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疏義曰:《詩》曰:椅桐梓漆。蓋桐梓者,柔良之材,可以備禮樂之用,方其始生也,特拱把之小而已,人苟欲生之,皆知養之,以其柔弱也。及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可以中宮室器械之村,則伐而共之矣,以其堅強也。稽諸植物,猶以強而先伐,則堅強者死之徒,何獨於人而疑之?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疏義曰:柔者,道之剛,故常勝之道在柔。弱者,道之強,故常不勝之道在強。蓋積於柔而成剛,積之者在其先。積於弱而成強,成之者在其後。先者在上,後者在下,堅強固居上,柔弱固處下矣。即天地以觀之,天以積氣,職生覆而位乎上,積氣非堅強也。地以積塊,職形載而位乎下,積塊非柔弱也。即物理以觀之,水之為性,次之東則東,次之西則西,而攻堅強莫之能先。風之為物,指我則勝我,我亦勝我,而折大木唯我能之,則以積眾小不勝為大勝故也。勝者在上,則不勝者斯為下矣。老氏之道術每得於此,以謂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故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可謂得常勝之道矣。觀其書,論柔弱勝剛強者不一,有曰守柔,有曰致柔,又曰不敢以取強焉,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於是篇又詳言強弱之道。莊子謂以懦弱謙下為表,夫為表則非處下之道矣。昔孔子對子路問,強以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其亦守柔之道歟?孰謂老氏之書與孔子之道不合?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徽宗註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疏義曰:道之在天下,廣也包畛,纖也入箴,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何損益之有?自道而降,斯囿於物,域於氣而為氣之所化,麗於數而為數之所攝,一盈一虛,莫或已也。惟道超乎氣數,而為萬物之奧,故有氣有數者,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以注焉而不滿,雖益之而不加益也,酌焉而不竭,雖損之而不加損也,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之所保在是,人不得而去者也。且域中之大,天地與焉。天地雖大,然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消之而消,息之而息,或消或息,與時偕行,凡以天地空中之一物猶未離於氣數故也。夫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盛衰更代,成壞相因,固不逃於自然之理矣。惟天道任理而均,故無適而不得其中,若山殺瘦而澤增肥,水息淵而木消枝,嘖以牙者童其角,揮以翼者兩其足。高者惡其亢,則抑之使俯而就,不至於有餘而太過,下者惡其卑,則舉之使企而及,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彼四時,春夏先,秋冬後,徙而不留,各得其序,莫不趨於中焉。觀天之道,豈不猶張弓乎?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徽宗註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疏義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蓋盈者虧之,所謂損有餘也。謙者益之,所謂補不足也。損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其化均故爾。《書》以謂滿招損,謙得益,時天道其斯之謂歟?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徽宗註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煢獨而畏高明。 疏義曰:莫之為而自然者,天道也。為之而使然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惟人道累於使然,故人心惟危,莫得其平,下者排之使愈下,上者進之使愈上,逐物俯仰而無持操,所以虐煢獨而畏高明也。煢獨可哀也,苟或見虐,則莫勸其作德而為善者,執為之長?高明可藐也,苟或見畏,則莫懲其作偽而為惡者,孰為之消?是乃損不足以奉有餘而已,豈知自然之天道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徽宗註曰:不虐煢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疏義曰:煢獨者,眾之所違而虐之,苟曰好德,則雖榮獨,必進寵之而不虐,是罄者與之也。高明者,眾之所比而畏之,苟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是饒者取之也。誠如是,其知道乎?蓋道者為之公,不偏於彼,不廢於此,泛應曲當,考不平以至於平,聖人體是,以用天下,孰有偏詖之患哉?然則損有餘以奉不足,非與於天道,孰能致此?莊子曰:主者天道。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徽宗註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帷不欲見贊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疏義曰:至無之中,化出萬有,聖人體至無,以供其求,豈恃其為哉?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孰有自伐之心乎?鳥所謂至為去為者以此。豈居其功哉?功蓋天下,似不自己,去功與名,還與眾人,孰有自滿之志乎?所謂神人無功者以此。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所謂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積眾小不勝為大勝,所謂人皆求勝,己獨曲全也。凡以不欲見賢故也。列禦寇驚五漿之饋,有在於是耶?帷不欲見賢,故謙得益而常無損,其得天之道矣。與夫飾智驚愚,修身明汙,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蓋亦異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徽宗註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疏義曰:水由地中,行無所不通,鑿之斯為井。道之在天下,無往不存,得之則為性,故《易》以井喻性。井養而不窮,改邑不改井,則以一性之常,不以貴賤加損,不以愚智存亡,雖事變無常,而其本不易,猶之井也。蓋天一生水,離道未遠,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舉天下之物,曾無以易之,故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彼物得以易之,則是徇人失己而失性之常,烏能得常勝之道而能勝物哉?惟無以易之,則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雖有曲折萬殊之變,而一常自若,可謂物無得而勝之者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徽宗註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疏義曰:智所以窮理,仁所以盡性。蓋天下之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智足以窮理,而仁不足以盡性,則是猒於所守,無持久之誠,其何以行之哉?柔勝剛,弱勝強,世俗之人,智非不足以知之,常患於不篤志以存之故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何益於事哉?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與此同意。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徽宗註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義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故江河合水而為大。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故丘山積卑而為高。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大人合并而為公。《傳》所謂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正謂是也。蓋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唯道集虛,而聖人之治虛其心焉,故能體道之虛,群實皆在,所攝所受彌廣。惟為物之歸,則萬物皆往資焉,而所制彌遠。蓋五土之神為社,五穀之神為稷,為社稷主,必欲滿而不溢,高而不危,非受國之垢不可也,與莊子所謂受天下之垢同意。興事造業,而其一上比為王,故王以歸往為義。為天下王,必欲持其盈而不溢,守其成而不虧,非受國不祥不可也,與經所謂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同意。夫受國之垢也,受國之不祥也,皆榮辱一視,而無取拾之心故也,要之虛而能受而已,故《道經》言: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正言若反。 徽宗註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則言豈一端而已。然至言不出而俗言勝,故有堅白異同之論,芒然不知所歸,天下始以正言為反於物矣。惟得言之解者,雖反於物而合於道,則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天下之至正,孰有過於斯者?莊子以寓言為真,蓋謂是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徽宗註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恢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疏義曰:鏌干無心於傷物,故復讎者不折。飄瓦無心於傷物,故忮心者不怨。常有司者殺,則人之遇之,猶鏌干飄瓦而已,是以天下平均,故無餘怨。且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若乃以聰合驩,是愛人者,害人之本也。禁攻寢兵,是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以此和大怨,其為善果安在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徽宗註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喜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疏義曰:聖人虛己以遊世,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直以循斯須而已,虛靜之中,何所湮汩?莊子所謂循大變而無所湮是也。故能泛應酬醉,受而喜之,未嘗棄人絕物,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也。為無為,事無事,處物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是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然契有左右,左契所以予,右契所以取,執左契則不從事於物,予之而已。雖予之而不責於人,則物之來也,不約而自孚矣。 故有德司契, 徽宗註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疏義曰:德之在人,同焉皆得,不可擅而有之者也。聖人調而應之,德廣所及,以心之所同然,還以分之而已,則人之契合者,固不期然而然矣。莊子載管子之言曰:以德分人謂之聖。此之謂也。苟卿亦曰:君子潔其辮而同焉者合,善其言而類焉者應。意與此同。 無德司徹。 徽宗註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玆徹也,柢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疏義曰:几物之量,未始有窮,物物求通,繁不勝應,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矣。聖人去智與故而循天理,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感而後應,皆緣於不得已,豈樂通於物哉?彼昧者不能以深為根,以約為紀,逐物忘返,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弊弊然以通物為事,而有和怨之心,將以為徹,祇所以為蔽。莊子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不其然乎?蓋樂通物,則因物有遷,或至於失己,其為蔽蒙孰甚,故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蓋蔽以言其不通,蒙以言其不明,累於物而有礙,孰能損實為通,致虛為明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徽宗註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疏義曰:天道任理,奚親奚疏?天道無私,奚取奚予?雖無松於取予,其因物以為心,唯善人是與而已。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善人之所從,民則從之,宜其常與善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以積善成德,故天有以與之也。是篇言執左契而終之以天道,以見聖人與天同道焉。惟其道與天同,此《洞酌》之詩所以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徽宗註曰:廣土眾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猒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疏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土宇彌廣,生齒益眾,皆不離於丕冒之域,而此必取於小制國、寡聚民者,何耶?蓋以廣土眾民,巧偽日滋,事則繁而不勝應,智以詐而不勝察,遷德淫性,觸刑冒禁,後世所以不治者,皆自此始矣。老氏憫當時習俗凋弊,乃推原道德,發明奧義。寓之於書,以破聾績,直欲易周末文勝之弊俗,還太古淳厚之風,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自容成氏、大庭氏至于伏羲氏、神農氏,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亦使民無知無欲而已。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若此之時,亦至治已。老氏立言垂訓,亦欲斯民復乎古初者也,故及於此。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徽宗註曰:一而不黨,無眾至之累。 疏義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惟其同德,則無所事比,而自養者已足,所謂一而不黨者也。蓋一者性之所同,而不黨者無所事比。同而無所比,則相忘於澹漠之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什伯之器無所用焉,又烏有眾至之累耶?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舜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樂推不猒,眾至而歸之,舜不容於辭焉。蓋所以感而應之者,特塵垢粃糠,帝王之餘事爾。若乃有天下而不與,坐致無為之治,非至神而何?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徽宗註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疏義曰:凡民之情,莫大乎養生喪死無憾也。其生可樂,則仰事俯育有所給;其死可葬,則衣衾棺槨有所備。無欣欣之樂,無瘁瘁之苦,又烏有輕死而不安土者哉?周之盛時,以保息六養萬民,而貧窮得以恤,以本俗六安萬民,而墳墓為之族,五黨足以相賙,四閭足以相葬,出耕同田,入居同廛,利則同營,害則同禦,民不輕徙而之四方者,亦以生可樂,死可葬而已。又況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則其重死而不之四方也宜矣。然而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政其所惡則散。治古之民所以重死而不遠徙者,以上得其道,有以愛之利之故也。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民不遠徙,非得其道而何?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徽宗註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息,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義曰:性分之外,無非物也。與物為偶,則外游是務,欲慮滋起,轉徙馳逐,莫之或已。有以致遠,則山必蹊隧而通,有以涉難,則澤必舟梁而辦,雖欲休影息迹,不可得矣。惟至德之世,民復其性,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而不相往來,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平易恬惔,無絕險之述,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是非兩忘,無攻戰之息,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亦各安其性分而已。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徽宗註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疏義曰:法之在天下,必有以記久明遠以貽將來者,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夫言有所不能紀,則證之於書,事有所不能信,則別之以契。至於治極無為,民淳事簡,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方且當而不知以為信,雖結繩以紀其要已,足以孚天下之心,又何假書契之詳密,然後使民不相欺哉?所以復結繩而用之者,欲還民於太古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徽宗註曰: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疏義曰:民復性則棄末,棄末則敦本,不作無益,不貴異物,所賴以終身者,田桑之事而已。是以耕而食,則穀人一於耕,識而衣,則絲人一於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智巧無所施也,日用飲食而已,故含哺而嬉。利害無所攖也,自適其適而已,故鼓腹而遊。民之能事已此矣,於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四者之外無餘事也。甘其食,在於止分,不在於猒飲食。美其服,在於去華,不在於服文釆。安其俗於不擾,無妄動之失。樂其業以自足,無歆羨之求。非民復其性,何以臻此?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徽宗註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疏義曰:居相比,則其迹為甚親。聲相聞,則其處為甚邇。宜其相保相受,相賙相賓也。乃至於澹然兩忘,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不知禮之所將相與於無相與故爾,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可也。性復樸而無欲,心忘物而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非至德而何?老子於太上章言:百姓謂我自然。蓋於太上之治既言百姓謂我自然,則知至德之世,民莫之為而常自然者,無足疑矣。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 疏義曰:道非言,無以闡其奧;言非道,無以立其本。道之出言,淡乎無味,根於理義,不特芻豢之甘,膏粱之美也,可操以為驗,可稽以為決。合若符節,正而易行,故關百聖而不慙。堅如金石,要而易守,故歷萬世無弊。然則信言之本乎道,又何貴於美耶? 美言不信。 徽宗註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故不足於信。 疏義曰:貌言無實,無實者華而已,故貌言為華而至言為實。從事華辭,貽非辭達,以支為旨,貽非體要,若然則去道彌遠。雖終曰言而盡道,足以美聞者之聽,求其根柢蔑如也,將何以示信哉?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徽宗註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疏義曰:趣完具而已謂之體,眾體所會謂之要,辭以體要為尚,則得道之大全,而貢於至理。以此立言,莫不當法,雖不假辮論,而精義具存已,足以猒人之可欲,是謂善者不辮也。昔孔子繙十二經而曰:要在七義。孟子學孔子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而曰:予豈好辮哉?其言有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而楊雄以謂知言之要,其善者不辯之謂歟? 辯者不善。 徽宗註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辮道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不能守中,則多駢旁枝而畔於道,非天下至正也。如公孫龍之詭辭,惠施之多方,殆猶一蚉蝱之勞爾,此所以為不善。 知者不博, 徽宗註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疏義曰:道要不煩,知其微者,悟於一言,存於目擊,少則得之,何以博為?經曰:博之不得名曰微。探其微,則無形而隱矣。惟反要而語極者,然後可以知此。莊子曰: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博者不知。 徽宗註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 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辮之不必慧。 疏義曰:為學日益,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有以多為貴者。至於為道日損,則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何取於聞見之多哉?善進道者,有曰守約,有曰說約,信所謂不如其約也。老氏應孔子至道之問,且曰:博之不必知,辮之不必慧。則知道之至妙,殆非多聞見可得而知也明矣。 聖人無積,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徂。 疏義曰:道之至虛,未始有物。物量無窮,皆域於道。道冥於無,則虛而能應;物滯於有,則其與幾何?若草之所盛,取之如殫,籄之所與,有時而匱,是有積者故不足也。至於虛而無積則異於此,若鑒對形,妍醜畢見,若谷應聲,美惡皆赴,所謂無藏故有餘也。聖人體道之至虛,運而無所積,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時出而應之,特其緒餘爾,未始礙於實也,所以能兆於變化而獨成其天歟?莊子論天道帝道與夫聖道,皆曰運而無積者,此也。孔子得是道,至於奔逸絕塵,反一無迹,非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也,故曰:丘以是日徂。雖然彼已盡矣,又豈溺於虛寂,使學者終不得其門而入耶?特不膠於有迹,與之兩忘於無有而已。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徽宗註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疏義曰:道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注之不滿,酌之不竭,贍足一切而未嘗費。凡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政其生成者,皆往資焉而不匱,亦以運而無積而已。聖人得乎道,未嘗擅而有之,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應酬醉之用於虛靜之本,至該至徧,隨取隨足,所以供其求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徽宗註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疏義曰:乾,天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化機密移於太虛之中,闢而生之,施而運之,物由是而成。凡萬寶畢昌於亨嘉之會者,無非以美利利天下也。《詩》歌豐年有曰:多黍多秣。蓋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必以多言之,以見天之美利無所不及也,雖不言所利,而利在其中矣。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美利。如此又何害之有?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徽宗註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鑒;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出于無為,體天而已,何爭之有?玆德也,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疏義曰:聖人以道往天下,因物之性,輔其自然,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所謂動善時也。供物之求,自無適有,應而不藏,其靜若鎰,所謂守靜篤也。赴物之感,柔靜自若,故和而不唱,其應若響,所謂守其雌也。是三者,在己無居,形物自著,非無為也,非有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雖建立萬法,而為出於無為,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天之道,一氣自運,品物咸亨,無為而常清,不爭而善勝。聖人體天以御世,與造物者遊,其道密庸,動而緯萬方,靜而鑒天地,泛應酬醉而無所於忤,故為而不爭,玆德也而同於道,故《德經》終焉。老子於《德經》之終,必以同於道為言者,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德總乎道之所一,惟德進於道,然後可以言德之至語。 道德至此,則作經之旨不其深乎?竊嘗論之,夫無言而道隱,不若有言而道明,老氏憫當時文勝之弊,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將以復其性情,而還之太古,著書九九篇,發明道德之意,以啟迪天下後世,非得已而言也,故於終篇序其作經之意,以謂信言不美,辯者不善,蓋欲使學者因言以探賾,得其所言,以造於忘言之妙也。亦若莊周之書終於《天下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自以謬悠荒唐,松其著書之迹。嘗歷考諸子,智足以知聃者,無過於周也,其書相為表裹,豈特言辮之間哉?迹其論六經之所導,不過《詩》之志,《書》之事,《禮》之行,《樂》之和,與夫《易》之陰陽,《春秋》之名分而已,豈在於章句之末?是知者不博也。及其論眾技之所長,自墨翟而下,至於惠施之多方,其書五車,舛而不合,駁而不純,去道愈遠,是博者不知也。以己獨取虛言之,則聖人無積可知也。以徐而不費言之,則為人愈有,與人愈多可知也。觀聖人育萬物,和天下,必以天為宗,以見天之道利而不害也。觀建之以常無有,必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見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也。謂老莊之書其言不一,其道不約而契,考其終篇之意,是為得之,謹論。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竟
 下旋
下旋 左旋
左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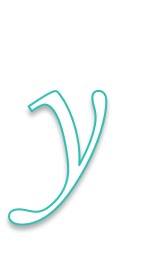 上旋
上旋